(來源:Mahen Bala)
開放跟包容不應只是口號,在學術研究上加以實踐也並非毫無困難。我們很容易看到他人的短處,卻忽略了自身的盲點。華人民俗研究十分貼近庶民日常,又是如此豐富且多元,學者及公眾不免從各自的背景、認知、訓練及生活經驗做出論斷,研究者在重視研究方法及資料詮釋的同時,更需要打開視野及心胸,各美其美,悅人之美,終能成其大。
【文/陳琮淵】
籌劃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至三日線上舉行的「第四屆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台灣與馬來西亞的比較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工作坊),對作者本人而言是一個有趣且難忘的體驗。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國際研討會每兩年一度,過去已舉辦三屆,是一個相對成熟且有一定號召力的學術品牌(intellectual property),此次由淡江大學東南亞史研究室及新紀元大學學院東南亞學系合辦,會議中別出心裁的設置,當屬定調「台灣與馬來西亞的比較視野」為研討主軸,以及舉辦「陳耀威先生紀念專場」,既體現了會議的核心理念,也扣問了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的最近進展及可能性。由於我自己過去並未從事地方風俗、民間信仰等傳統意義上被視為民俗領域的研究課題,會議所呈現的論文亦將在修訂後集結出版,故不在此論述議程梗概及各方面的優劣得失。而是有感於辦會過程及由此延伸出的討論中,讓我重新認識並思考了相關議題,確信華人民俗研究是一個相當重要且具延展性的領域,能夠吸引來自不同學科訓練的學者共同合作、深入探掘。
首先是關於華人民俗研究的視野(角)與「理論」,本次會議的兩場主題演講,皆部分涉及這方面的議題,李豐楙及林美容兩位教授從各自的研究經驗出發出,演示了概念分析及比較研究如何具體操作,對於台馬兩地華人民俗學界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也平衡了會議以馬來西亞方學者為主的篇次分布。當然,他們的出發點(問題意識)及研究經驗,未必全然適用於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研究領域,由文獻整理及田野調查所形成的在地觀點仍然十分重要。而比較研究,或說更初階的相互參照,不僅是推動社會科學研究進展的重要基礎,也夠破除一些既有觀念及自身認知的固化框架。此次會議中學者的發表及與會者的提問,顯然很好地達到此一效果。與會者由此得知,原來台灣跟馬來西亞的華人民俗有相似與不同之處,這些對照性的經驗分享,或許能在不久的將來轉化成研究選題或論述基礎。

(來源:東方日報)
不只是民俗研究
我聆聽各場次發表所得到的另一個感想則是,概念或理論的分析,絕非將某本教科書或某位名家所提生搬硬套到自己的研究當中,而是系統性地去考慮問題、收集資料,從而把複雜的現象收束到簡潔確切以利分析掌握。此一過程,無疑是科學研究追求經驗性因果解釋的必經之途。然而包括華人民俗在內,所有涉及人類心智創造及人群互動的研究,皆有其高度複雜性及主觀詮釋的空間,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是必須的,方法的應用上卻未必只能唯一、固定;民俗學、宗教學、人類學與華人民俗研究對標對味,從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學科入手,也能有其獨到的貢獻與發現,投入的議題或領域帶有跨學科性質,不代表個別研究者「必須」跨學科或只能固守本身學科,依據研究選題及需要,認真的學者自然會找到最合適的方法,無論其源自單一或多個學科。所謂「真積力久則入」得到其他學科廣泛認可的精深研究,難道不是一種「跨」學科實踐?
其次是華人民俗研究的多樣性與滲透性。過去我曾一度以為,華人民俗研究無非就是華人民間信仰研究的變體或擴大,似乎以民間文史工作者的投入為主,大學中除了宗教、歷史、文資保存等系所,少有學者投入,總體也會更多專注在民俗采風及田野踏查之上,出版亦較偏向掌故漫談及資料集成。然而會議本身及籌備的過程讓我意識到,華人民俗研究遠比我想像的更多元且寬廣。無論在台灣或馬來西亞,華人民俗有其堅韌的生命力,民俗傳統不斷變化流失,也正被創造和發揚,從鄉音曲藝、慶典儀式到信仰習俗,無不是華人文化與價值觀(群我、人地、故土與他鄉)的體現。例如,文學研究者從文本分析入手,挖掘神話、小說創作的民俗意涵,歷史學者探索民俗與社群(方言群)遷移的關係,地理學者帶入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等研究技術,社會學對於性別及結構性議題的關注,皆有助於豐富並夯實華人民俗研究的方法論基礎。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華人民俗研究的滲透性,從這次會議的一些發表中不難看出,民俗活動往往離不開特定人群的組合與連繫,因此研究民俗可以不只是民俗的研究,還可以擴展至華人政治、社團、商業、藝術、音樂、文化、體育等,探討其流傳、變異與再造。而這些領域的相互滲透,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各地華人社會的性質及發展路向。
無論是視野的擴大及方法的應用,皆仰賴開放的心態。學術會議並非論文指導,更非文壇比武,是討論學術問題而不是評斷學者是非;更何況每個領域、圈子及學者皆有專業發展脈絡及自身侷限,很欣慰與會學者及參與者所展現的高度風範。特別是兩位主題演講者研究經驗豐富且著作等身,卻都難能可貴地抱持著高度的學術好奇心及謙卑身段,學問品格皆令人十分欽佩。比如,林美容教授與作者通訊回應學者稱道時說:「我没有大學者的架勢,我只做頂尖的二流學者。…不是客氣啦,比較能立於不敗,又能挑戰一流學者。」;甫當選新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李豐楙教授回覆作者致賀電郵時表示:「……(當選院士)這是對於宗教學界的肯定、縱使冷門,只要努力還是會有成果的。」這種不自鈐於高度專業成就,堅持信念,而以紮實謙和的態度做事待人,也讓我想起陳耀威在馬來西亞華人民俗等領域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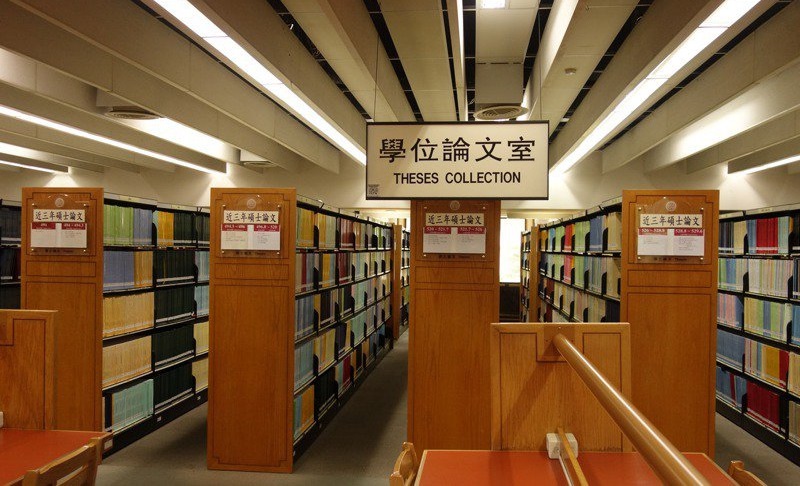
(來源:聯合報)
思索學術健康發展
第三是會議未直接討論卻十分相關且重要的是:學術語言及平台議題。包含本次會議在內,過去幾屆的華人民俗研討會皆以華語(中文)為學術語言,相關成果也多以論文集形式出版,是否有越走越窄、固步自封的疑慮?本人對此採取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只要華人民俗研究本身的吸引力、學術價值足夠大,便能不斷吸引各種語源及學術訓練的人才投入,共同壯大陣容取得更多成果。目前大學考評機制受到商業化學術期刊資料庫推廣的影響,或多或少固化了既有優勢語文的學術優位感,也連帶影響了學者的研究選題及發表取向。撇開某種功利思維,語言掌握(語言學等少數學科除外)不應該成為學術的邊界或研究成果優劣的判準。「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研究專以發表及交流為導向,而非追求真理樂在其中,真的是我們應該走的唯一之道嗎?我想起某次受邀到以語言教育聞名的大學演講時,途經正在以英語講授研究方法的課堂,心想此處真是卓越,必定能培養出一流國際人才。然而在演講交流環節,卻有學生提出他其實無法適應,方法論已經夠抽象困難的,復以語言的隔閡,簡直是盲人摸象,既沒學到方法,也沒精進語言,對此感到無所適從。同時也有學生問到語言與研究的關係,是不是一定要先掌握好語言,才能做好研究。記得當時以如下提問開啟我的回應:「有沒有可能當您精通了研究所需的各種語言及研究方法,您已經到了快退休的年紀;或是您的語言跟方法持續變強,論文卻老寫不出來,先被迫休學、退學、離職了?」我想說的是,無論是語言或方法,研究者或需有所追求,但不必給自己或彼此置設太多前提。
我們固然鼓勵學者跨出同溫層與舒適圈,嘗試挑戰自我追求突破。但這絕不構成貶損抹滅依據自身語言能力及學科訓練進行研究、選擇發表平台者貢獻的理由。更有甚者,我們也有必要反思過度重視特定發表語言(如英語)及平台(如特定資料庫期刊)的拜物教(fetishism)式扭曲,長期而言是否真的有利於學術的健康發展。
開放跟包容不應只是口號,在學術研究上加以實踐也並非毫無困難。我們很容易看到他人的短處,卻忽略了自身的盲點。就我個人而言,此次辦會最大的收獲之一,便是了解到自身的不足與局限。華人民俗研究十分貼近庶民日常,又是如此豐富且多元,學者及公眾不免從各自的背景、認知、訓練及生活經驗做出論斷,研究者在重視研究方法及資料詮釋的同時,更需要打開視野及心胸,各美其美,悅人之美,終能成其大。
 陳琮淵 |
臺灣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兼任《淡江史學》、《臺灣東南亞學刊》、《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及《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編輯委員。他同時也是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國際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東亞及東南亞發展、婆羅洲研究、華人族裔經濟、經濟社會學及企業史。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按贊和追踪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