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日報)
我們現在怎樣做傳媒?環顧今日身處夕陽行業的報人,愈走愈窄,愈長愈像,更甚者報格全無,淪落至惡俗,以戲為文的低端品味,沒有一毛價值。傳媒從未像現在這樣意識到自己,除了本國政治新聞外,上稿時可以無需負任何責任。那些返祖現象,所反映的不過是華社自身淺薄的痼疾,才不是什麼網紅化,而是思維上的怠惰滯後,得過且過,喜歡忸怩作態,調和折中。再加上網絡迷航,天天發諧音哏的白日夢,與不思考無常識的群氓,恰是天作之合,笑嘻嘻,綁在一起往下沉。
【文/方美富】
假如今天要研究二十一世紀前面十年的知識界精神史,媒體沉浮錄是否適合當作切入點?輿論之驕子梁任公想必舉手支持列入他的專題史。《東方日報》是二〇〇二年才出現的年輕報章,這段時間評論界未必萬馬齊瘖,卻絕對是滿街飛禽走獸的時候。又值讓人不齒,官商勾結《南洋商報》收購事件,華文報大一統之勢已成,作家接連離開了原本的發表園地,思想真空之大,只能由唐老鴨、笑面貓、大肥象、指鹿、斑點老貓、大恐龍來替代。毫不誇張,馬來西亞評論名家,文化人,知識人,不是停筆就是轉移陣地,發出匡時的爭鳴。它的受命與旨趣由誕生開始就已經注定。
以整個華文報學史從馬六甲出現的一八一五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算起,與十多年的報社歷史一比,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依《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題辭「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挖掘其間的蘊涵深意,不妨審視現在的媒介尚有啓迪民智而存在的理由嗎。報章有義務庇護生命的尊嚴,對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抱一種同情,引領輿論,則人人都是「博愛者」。以言論起家,更是骨幹,報變之後的最後一方淨土。
 ■《東方文薈》部份作者欄目: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東方文薈》部份作者欄目: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我傾向應以二〇〇七年六月三十日作這份報章的分界,歷史地位前後完全不同。旗下《東方文薈》二〇〇五年五月一日第一期的自我期許,是回顧歷史的滄桑,以人文批評為主調,隨便繙繙創刊時幾篇題旨「沒有知識份子的知識年代」、「新馬已無陳六使」、「重訪一九八〇年代」、「不死的流亡者」,可以想見思索者的眼界甚高。幾期後,主持人張景雲先生寫了一篇重要的編後記〈大氣象的締造者〉,開宗明義解釋為什麼我們的社會需要人文評論,而且必須來自在地的聲音,摒棄過去剪貼港臺專欄填版的習性,任何意見都不應缺乏主體性,正式宣告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註一】此處難以盡述文薈如何為普世價值的傳統護航,塑造公共輿論空間的實踐,借用百期紀念時潘永強的盼望,興許得以說明編輯的志願,「一,堅持本土關懷與在地視角,原汁原味絕不摻水。二,不分門戶,無黨無派,除朝廷爪牙阻撓以外,不設封殺名單。三,尊重作者,選用長稿,發掘題材。否則大馬再大,張少寬、萬家安、李亞遨、李業霖等人大作,也許無報可發表。沒有文化副刊,沒有文化雜誌,談再多文化抱負,報業傳統,都是虛幻與魔幻」。【註二】
這份副刊,加上聲名在外的〈名家〉,得以短時間內吸引眾多「非順民」投稿,不約而同參與一段訂偽貶俗,對社會有所擔當的歷程,心甘情願交出篇篇「思想的初稿」,原因在此。魏月萍的「思想追緝」、潘永強的「自由深淵」、許德發的「遠處蒼穹」、MK Sow的「冷熱咖啡」、蔡長璜的「藝文風景」等等「締造者」欄目,一時間氣象萬千,又何懼無路。
值得注意,此時輿論環境之所以能夠做到「草木繁盛,慎密思辨」的編輯宗旨,很大原因是國內的學術環境正在起變化。不少作者擁有極好的思維訓練,學理與表述能力俱佳,部份作者更是經歷從碩士到博士的階段,漸趨成熟,文章充滿高遠的想像力。學識存養的這份自尊自信,視報社的供需關係為平起平坐。過去聽到「華社三支柱」一類的話,頓時失去常理的能力,對他們則完全無效,沒有過度矯情的遐想,無可無不可。這時日,對彼此都是學術青春期的反叛,如今的「東方遺老」回望,也是記憶所繫之處的「舊日好時光」。一家報社的江湖地位不是三朝五日建成,但是摧毀只要彈指。彼時主持是張景雲、劉敬文、謝偉倫的社評三先生,固執於那種完全清醒冷靜的風格,突然一天館方宣佈報紙社論收了,不啻韋伯理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後來方向,那已經是另一番天地了。自殺自滅的消息傳來,我永遠忘不了當下的錯愕,那是李碧華《630電車之旅》的一句話,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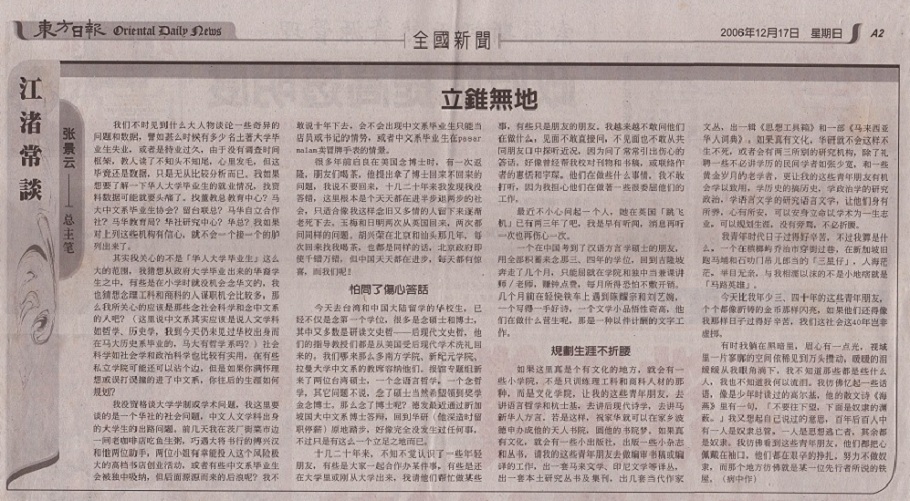 ▲「立錐無地」勾起讀書人多少傷心事。
▲「立錐無地」勾起讀書人多少傷心事。
 ▲《東方青年》永垂不朽。
▲《東方青年》永垂不朽。
毫無疑問,前五年是它自身歷史的高峰。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景雲先生〈立錐無地〉,那是歷經人間疾苦後的洗練。讀書人注定窮途末路的宿命,還引起黃錦樹、張錦忠、溫任平、梁靖芬同聲一哭。【註三】你記得嗎,林宏祥主編《東方青年》對「真默迪卡」的詰問,那些年我們慶祝的國慶日本身就是個大問號,這才是「八九點鐘太陽」的先見之明。他還收集大街小巷塗鴉隱含的譏諷,頗有「觀風俗知得失」的意指,那是華文報最早注意Fahmi Reza的藝術抗爭。不久政治壓力一來,無可避免的命運,受到絞殺,青年還沒講夠就要閉嘴了。那是言論版一不小心略談罷工抗議,明天專欄就會歸西的黑暗世局。二〇〇四年我是助編,坐在大門右一,可說是編採部最下遊的職務,尤以言論組的版位最常經手,對查禁的境況很感好奇。報人眼中無英雄,老早就曉得「太上總編輯」(們)的威力,完全講不出一句好話,說也奇怪學界何以捧得那麼厲害。還有還有,陳富雄那枝出眾的報導之筆。他訪問一號人物普騰汽車首席執行員,一張只值六毛汽車入口準證表格,惹得AP之王Nasimuddin與時任貿工部部長Rafidah一身蟻。那是記者胸膛的徽章,各大語文報競相引述,風波越滾越大。可見當時若干文章和政論,還是比較負有自由和批判精神,在那個時勢成為一種力量。
梳邦時期共事,就是一群人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向來就是此意,正因外在的言說空間狹小,處處圍堵,在那些陰影跌下,有個很特別的傳統,專門吸引有抱負的人。現實的困境使員工好喜歡同上司吵架,流傳最久沒有消滅的是,報社培養了一批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拒絕認命的不老青年。不只是爭辯公器私器,細至幾乎是連重要新聞要怎麼做,國際大事件攸關公正那條線要劃到哪裡,時時都有這樣的爭論。二樓專題記者更是每每跑來編輯部,「這篇猛文!」喜不自勝又一點點不好意思,我又來了。咦!既說猛,應該無瑕可擊,還來改東改西,不如這樣,不如那樣,讓人懷疑是不是患有嚴重失眠症,老是不回家。那些日子遂想起《晨報副刊》徐志摩的聲明,「辦好是我的功,辦壞是我的罪」【註四】,孜孜矻矻,奮力一搏的精神。報社建立了那個理想,又背棄那個理想。無數去職者縱然四處飄零,隨行總是未忘要帶上那簇火焰,熱情與初志,變成一股獨特淋漓的元氣。你知道那時的媒體環境,到底需要怎樣的操守嗎,那是委屈自己,輪流上陣化身「中華魂」自吹自擂的世代。
 ■「中文報章七一有變化:《東方日報》改小開板,星洲集團人事更動低調」,當今大馬中文版,2007年7月1日。
■「中文報章七一有變化:《東方日報》改小開板,星洲集團人事更動低調」,當今大馬中文版,2007年7月1日。
人心渙散始於三番五次的整頓,以不知哪來的調查顯示「只有五巴仙讀者會讀社論」,三刀五剁。社論存廢,本就不應視作商業資訊那般經營,砸碎一個好招牌。張生因之分道揚鑣,所謂「調查」與評論界的認知脫節太遠。為什麼要消滅社論這個問題,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以平庸為榮?一份報紙連千字空間都沒有?一週幾次毫無營養的「飯後禮讚」——杯觥交錯,吃喝玩樂的文辭,少寫幾篇就好了。那所謂「調查結果」不能說不是看法之一,但說不上合理,恐怕是本邦報業史上最無厘頭的「改革」。
據李星可那本兒「進步語言」寫成,隨處流露不可一世精神兒的報人回憶錄,裡邊兒提到那時候兒的報社,主筆往往比總編輯對一家媒體的前程更為重要,地位更高【註五】,從報紙的角色與責任來看,一點兒不錯。
需知主筆並不隸屬編採部,無黨無私,確保新聞與評議各自為政,得以保存獨立的立場,不作含混模糊的評斷。編採因身在其中,近乎鐵石心腸的趕下版,主筆既內在又超越的地位就突顯了。這一職志如同黑暗的目光如炬,無需糾纏於商業與政治的漩渦,說一些很委屈自己的話。《新海峽時報》刊登霹靂王儲Raja Nazrin Shah二〇〇七年四月三日,於律師公會的青年圓桌論壇的主題演講,值得一記。王儲七項建議要求社會各階層,應有歸屬感與共同體的使命,不拘族群,宗敎或血統,陽光普照無分你我,每逢面對宗敎自由與憲制危機的爭議,應當重新召喚聯邦憲法精神,「這個國家屬於所有馬來西亞人」。華文報偏偏獨漏的新聞,成了報社內部事先張揚的明日頭條,正是編輯會議時主筆景雲先生的獨到之見。其實落入讀者手上時,已過三天,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推託,然而對張生來說,要做的原因只需一個,警世通言不會貶價,針對各種紛擾有醍醐灌頂之效。半個月後,他以〈一圈一點〉再論此事,強調國家大法必須受到重視,因為不遵守憲法者往往是掌握公權力的公家機構,不僅無法保障基本人權,出版自由,甚而利用印刷與出版法令,官方機密法令,箝制言行。百姓不應生活在滿目瘡痍制度之下。如此辦報,不僅是「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的眼光,同時需要過人的膽識。博雅君子張景雲,無疑是新聞學的最佳敎材,最震撼的一次敎育。
 ■胡蛟,〈謹向全馬華人進一言〉,《星洲日報》1959年8月1日,版9。
■胡蛟,〈謹向全馬華人進一言〉,《星洲日報》1959年8月1日,版9。
媒體機構畢竟不是宗族同鄉會,文明利器必得引導讀者,不計一切榮辱當一隻看門狗,監督社會脈動,做一名人道主義者。大多數人不懂法律,於是報社鐵肩,有其道義扛起與社會大眾溝通的橋梁,方能形塑民主法治文化。報人的自尊自重就要如此維護,也是他存在的緣故,那就不是早一天還是遲一天的問題了。但是我們媒體的墮落已經不是一兩日的事,言論自由固然無價,一念之間能夠以各種理由輕易退讓。李星可因一九七一年兒的「五月風暴」,因言獲罪被李光耀政府逮捕下獄,自有外人視為鬥士兒的榮耀。可是,同一個人兒早在一九五九年,居然將社論當工具兒,出謀獻策讓胡蛟掛名讚揚Tunku Abdul Rahman的聯盟(Alliance),大選時鼓吹華社兒「要穩定,不要亂」式的抉擇。用以換取兒支持《星洲日報》北上開拓馬來半島市場,更廉價購得五十英畝的社址兒【註六】,很有炫耀的意味,絲毫不覺臉兒紅。
環顧今日身處夕陽行業的報人,愈走愈窄,愈長愈像,更甚者報格全無,淪落至惡俗,以戲為文的低端品味,沒有一毛價值。傳媒從未像現在這樣意識到自己,除了本國政治新聞外,上稿時可以無需負任何責任。那些返祖現象,所反映的不過是華社自身淺薄的痼疾,才不是什麼網紅化,而是思維上的怠惰滯後,得過且過,喜歡忸怩作態,調和折中。再加上網絡迷航,天天發諧音哏的白日夢,與不思考無常識的群氓,恰是天作之合,笑嘻嘻,綁在一起往下沉。
我們現在怎樣做傳媒?我希望有人好好寫一部言論的百年精神史,看看如何摧毀你的人間情懷,削弱你的誠信。如果有一天究問報刊的高峰,過去,現在,未來的話,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張生在那裡,那裡就是。
【註解】
一、張景雲,〈大氣象的締造者〉,《東方日報•東方文薈》2005年11月6日,版A13。
二、潘永強,〈文薈百期祝願感言〉,《東方日報•東方文薈》2007年4月1日,版3。
三、張景雲,〈立錐無地〉,《東方日報》2006年12月17日,版A2。黃錦樹〈老輩知識人的傷心之言〉,同見《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2019年,頁205-213。
四、徐志摩,〈記者的聲明〉,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二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15。
五、李星可,《亂世滄桑》,新加坡:中外翻譯書業社,1991年,頁106、167。
六、李星可,《亂世滄桑》,新加坡:中外翻譯書業社,1991年,頁150。
 方美富 |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