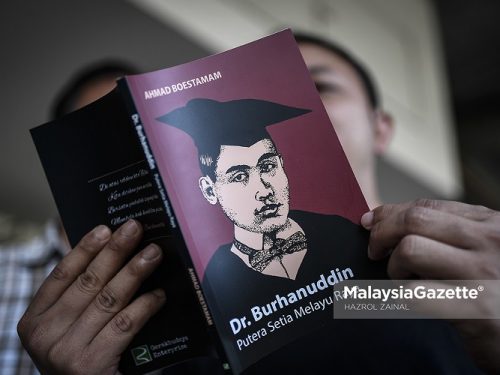(來源:Malaysia Gazette/Syafiq Ambak)
道德與倫理之間並非只能二選一,個人對政治人物誠信、對公義的追求還是非常重要。歷史上無數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吹哨人之所以可以為公共利益罔顧個人利益,憑的是道德勇氣;在國陣統治期間無數大馬人罔顧後果違法走上街頭,憑的亦是道德感召。在倡導理想價值觀的同時,我們該意識到我們所處的環境並沒有那麼理想,進而避免只從道德觀點出發看問題,而是同時考慮到現實的局限、選項及各選項的好壞。如果經過這樣的思考過後還是選擇向良心負責或選擇向政治現實妥協,那才是真正負責和值得尊重的個人選擇,就如韋伯所說,才是一個真正成熟的人。
【文/陳慧思】
政治學者黃進發早前在《當今大馬》發表〈509反思:民主需要好人專業地分裂〉,獲評論人兼社運人士黃業華的回應,雙黃在臉書展開了精彩的思想交鋒。觀戰未久即起草這篇文,主要是進發去道德的談法困擾了我,而兩年多來大家爭議的馬哈迪任相問題亦讓我思考這方面的倫理標準該如何確立,過後邊讀書邊觀戰邊調整想法方成此文。
進發主張在去道德化,確立政治倫理。他說,「倫理的確立則必須打破政治文化上的兩座大山:道德論述和犬儒思維」,這固然是對的,但他漏提了另一座明顯的大山:功利思維。本文主要是一篇分析文,無關我個人對馬哈迪任相的立場【註一】,只想嘗試釐清道德與倫理和現實利益的關係以及「馬哈迪任相」之辯的難題。
道德是我們的價值觀,倫理是適用於任何人任何時候或指定群體的一套價值判斷的標準或具有價值判斷的行為準則。道德是只知道向善的個體戶,沒有其他考量。倫理則根據一定的道德判斷規定在什麼情況下該有什麼樣的操守,以便可以給相關帶來長遠的利益,比如媒體該保護匿名線人,一來這是媒體的誠信,二來則是萬一媒體都沒有遵守這個行為準則,那以後還有誰願意給媒體爆料?所以針對特定群體而設的倫理是維護一個體制健康運作的行為準則。有別於必然向善的道德,倫理還須考慮一項行為準則是否能導向該領域最大和最長遠的好處。
進發後來在臉書分享了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政治為志業〉,讓我們能較清楚地看到,他想談的主要是倫理觀而非具體的操守。韋伯在該文中把倫理觀分成兩大類,一種是「信念倫理」(ethics of conviction),與「道德」意思相通,在政治上相當於意識形態政治;另一種是「責任倫理」(ethics of responsibility),即要考慮到自己行動的後果。對他來說兩者並非全然相抗,而是互相補足的【註二:第92頁】。韋伯的兩套倫理觀要求政治行為者(political actors)既要有道德,亦要為自己的行為或選擇所帶來的後果負責。
 (來源:BBC)
(來源:BBC)
去道德說欠妥
進發在臉書與業華交流時談及他主張去道德化、取倫理,或說鑑於馬來西亞的狀況他偏重責任倫理(而輕信念倫理)【註三】。偏重責任倫理可以理解,但去道德化之說則欠妥,因為有時道德即是倫理,政治人物若無一定的道德操守,政治及民主體制就難以健康運作,譬如我國無誠信的投機政客為私利跳槽,就破壞了民主體制(看到這裡想要給筆者扣衛道魔人帽子的讀者請耐心讀下去)。我們常說的政治人物要廉正、有誠信,即是英文的integrity,根據Cambridge字典的解釋,integrity是「the quality of being honest and having strong moral principles」,即誠實及具有高度道德原則。這是對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亦是倫理——政治人物必須信守承諾、不能在公務中謀私利、不能自己訂一套規矩自己卻做另一套等。我們可以英國最近的輿論作參考:早前蘇格蘭的首席醫療官卡德沃(Catherine Calderwood)在限制令期間回到自己的鄉下,違反衛生部自己定下的規矩,遭致排山倒海的批評,起初蘇格蘭首席部長史特金(Nicola Sturgeon)替她護航,但卡德沃最終還是在輿論壓力下辭職。後來英政府的科學顧問弗古申(Neil Ferguson)教授讓一個女人登門造訪,違反了政府勿互訪的勸告,在曝光後即辭去顧問職。最近首相顧問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被發現開車從倫敦送妻兒回265英里以外的杜倫(Durham),首相約翰申(Boris Johnson)替他辯護,但批評聲浪還是不斷。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英國社會對政治人物的誠信與廉正的高度重視:你是政府的一員或直接影響衛生政策的顧問,卻私下違反政策規定,這是誠信與廉正問題,如果沒有辭職認錯,要如何面對遵守政府規定的民眾?
英國高官會辭職,並不是因為他們自己良心發現,而是人民對政治人物有要求。若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對政治人物的廉正與誠信(integrity)沒有一定的要求,那麼政府及政治制度就難以健康運作,這恐怕亦是大馬政局跳槽成風的因由。在政治上各種利益與主張在相互競爭以影響政府的決策與資源分配,若有一部分人民主張政治人物該有誠信,然後繼續影響更多人,其擴大影響力以促成改變的機會就會更大。所以道德要求或信念倫理肯定在政治中有很大的存在價值,棄道德的談法欠妥。
須納入現實考量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現實存在各種狀況:社會認知的落差、政治結構、制度的問題和當下的政治狀況等等會導致種種局限,以致當下的選擇有限。在選擇有限的情況下,純粹的道德觀恐怕無法替我們解決問題。但與其說棄道德,我認為我們該問的是,在現實局限下,除了道德,我們是否亦該有其他考量?比如歧視及單一種族至上肯定是錯的,要求廢除憲法第153條款是忠於對公正理想的追求,是很基本的道德追求,但如果我們推動反憲法153條款的運動,恐怕會因政客及媒體炒作而加深族群之間的猜疑、導致社會動亂,更別說會遭逮捕扣留,所以大馬社會相當有默契地暫擱這方面的討論。但這表示我們應該完全放棄這方面的言說嗎?這樣的要求就如業華說的,忽視了個人的能動性(agency)。如前所述,個人的道德追求亦可以擴大成一股足以構成影響的社會力量。我認為與其要大家棄道德論,不如邀大家嘗試在思考問題時莫從單一角度(如道德或政治利益)出發,而是從道德、倫理、政治現實各方面思考:什麼問題該糾正過來、現實局限是什麼、我們的選擇有哪些、後果有哪些、我們的理想可以如何實現?盡可能誠實地、實事求是地釐清各個選擇的問題,才作出自己的最終選擇或判斷,避免好心做壞事,或只看見短期利益忽略長期建設。若是我們誠實地審視自己的考量和選擇,很大可能我們發現很多選擇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非黑與白的分別。這樣或許方能建立比較成熟的政治社會,也能讓我們對作出其他選擇的人亦能有多一些理解,而非動輒惡言相向。
 (來源:The Straits Times/EPA/EFE)
(來源:The Straits Times/EPA/EFE)
大家爭議的「應否推舉馬哈迪出任首相」這個問題有兩個責任倫理的面向:除了進發提及的,我們該對自己選擇的後果負責之外,還包括馬哈迪須對自己過去犯下的種種貪腐濫權錯誤負責(韋伯的〈政治為志業〉在這部分談的就是政治人物、公務員等該如何專業侍事、有何操守)。希盟選一個前科累累的人任相,放在任何倫理標準上,恐怕都很難說得過去,只能說這是出於現實利益考慮的選擇。既然如此,那需要檢驗的是,這個選擇是否選項有限情況下的最佳選擇?
回答這個問題關係到我們如何判斷最大的利益、目的的價值,以及對民意的解讀,實在是個大難題。有人認為換政府才能帶來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同時實現政黨輪替對民主進程影響深遠 ,並認定希盟得結合馬哈迪的力量才能成功換政府——這可能是對的(但我們可以質疑:大家都說希盟只收割了三成馬來票,馬哈迪是否真的對票房有那麼大的影響?)——但其可預知的後果是公民社會的分裂、另一個類巫統政黨的崛起,沒有預想到的後果則是馬哈迪拖延交棒(對一些人來說或是可預知的後果)、公正黨兩派無可彌補的大決裂。
有人則認為避免選腐敗背信前科累累的人任相保持道德制高點、維持公民社會的向心力才能促成制度改革,帶來最大最長遠利益,也未必要與馬哈迪合作或讓其任主帥才能實現換政府的目的——這也可能是對的(但當時的難題就是,安華還在牢中,希盟還有哪個適合的人選?如果當時選了阿茲敏有沒有更好?)——但其後果可能是無法換政府以實現第一次政權和平轉移,以致納吉繼續隻手遮天、破壞體制,疲乏的公民社會亦難有作為。
我們選了第一條路,就無法看到第二條路的風景,走這條路之後會出現什麼樣的景象實在難以估計,所以檢驗任何一方都會有不公平的地方:成功換政府後,選第一條路「希盟+馬哈迪」的人策略得到印證,但他們亦須接受現實的檢驗(兩年後政權就倒了,以致出現新的亂象,這樣做真的值得嗎?);選第二條路的人無法印證無需馬哈迪掛帥仍有可能換政府之說,但他們亦無需接受一旦換政府失敗情況會否更糟糕的現實檢驗。所以在自證或檢驗他人的時候,我們還須認清自己和他人的局限與優勢,才能避免寬以勵己嚴以待人。
眼前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政治人物的誠信問題。除了議員毫無誠信見利跳槽之外,希盟推舉的馬哈迪無疑已自證誠信有問題(一再拖延交棒甚至說出「幾時交棒隨我喜歡,可能是國會解散前一天」如此蠻橫任性的話)。如有要談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及廉正度是我們無法忽略的問題,無論是談倫理還是論專業,廉正而破除私利都是任何行業職員的本份,政治人物豈能豁免?在「是否該與無誠信或貪腐的政客合作」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政治現實是:若是我們要求政治人物高度廉正,恐怕臺上大多數人都要淘汰出局。或許我們該問的是:該設定什麼樣的標準?無誠信或貪污到什麼程度還可以接受?就算接納,要接納到什麼程度、是否需要經過時間的考驗?比如從黨員做起、獲准競選議員還是當主帥?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P)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P)
吹哨人的道德力量
現實的局限並非只會導致政治利益超越倫理,亦有可能是道德良知超越一般倫理。比如在1806年英國反奴隸貿易的國會議員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同僚在內閣設立新的《外國奴隸貿易法案後》保持低調避免該法案引起反對者的關注(Amazing Grace這部電影甚至描述他們想方設法阻止國會議員入國會議事,或有誇張成份),最終成功悄然促成新法的制定,豈非亦違反了一般政治倫理或該讓雙方充分辯論法案的程序正義?但若他和同僚沒有保持低調,可能法案會因奴隸主及政客整個利益集團的反對而無法通過,繼續殘害無數寶貴的生命。在這個例子裡,威爾伯福斯選擇了良知(道德)而沒有遵守政治倫理,我們該如何看待?就如進發提到的英國後座議員如哥賓當年的後座逆反(一共違反黨鞭四百多次——【註四】),亦是違反了有政黨倫理考量的黨鞭制,會造成一定的混亂,但國會議員在與良知攸關的特定課題上(尤其是女性和兒童福利的課題)可憑良知投票在西方民主國家亦是約定俗成,有的議員只是把這條線往上推而已。
另一個例子:一般行業包括公共機關都會有禁止員工把內部文件泄漏出去的守則,在一般情況下這當然是合情合理的工作倫理,但這些工作倫理亦可能是掩護濫權、鞏固貪腐制度的可怕機制,需要靠個人的道德勇氣與之抗衡。比如在1MDB課題中,我們要靠多少個冒著生命危險打破這個工作倫理的公務員、銀行職員等吹哨人把文件傳送給媒體,方能揭露1MDB的洗黑錢黑幕?
以上的幾個例子都說明,如果有很高的道德指引,打破一般倫理或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當然這總歸是個人價值觀判斷)。我會在「倫理」前加上「一般」是因為倫理會隨著社會經驗而改變,亦因問題的複雜化而出現爭議,韋伯談的公務員責任原則——理當根據政治人物上司的命令行事,哪怕他的信念告訴他這是錯的【註二:第54頁】——已遭到挑戰。雖說在一般情況下韋伯說的沒錯,但卻可能會導致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說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在歷史上無數吹哨人前仆後繼打破結構限制揭露弊端之後,吹哨人的重要性已獲得很多社會普遍認可,許多國家已制定法令保護揭露貪污濫權等黑幕的吹哨人,以維護公共利益,儘管在一些情況下吹哨人的倫理爭議依然存在,比如史諾登(Edward Snowden)是否該揭露保密文件依然存在爭議。在吹哨人的例子中,個人的道德追求(要求廉潔、誠信、廉正等)突破了一般倫理的結構性束縛,締造了新的倫理標準,這符合業華提的個人能動性可創造的可能性。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EPA)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EPA)
避免遭道德反噬
訴諸道德的問題在於,並非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價值判斷,如果社會的價值觀分歧極大,那麼訴諸道德可能會遭致反噬(當然訴諸現實利益而打破倫理規範亦有可能會遭致反噬,但這點很明顯恕我略過)。譬如,若是我們認同威爾伯福斯和同僚之舉,那麼如果政府認定守護民族利益是最崇高的道德,靜悄悄通過擴大單一種族利益或進一步損害平等的法案,我們該如何回應?在這個例子中,若我們追隨道德以致破壞議會倫理及程序正義,就要認知到個中風險。我估計這亦是進發的「棄道德,取倫理」之說想要表達的。最接近我們的例子是安華夢想透過跳槽換政府的「九一六變天」策略失敗,我們反倒迎來了霹靂政變和後來的喜來登政變。這一點進發的確提醒的是,在一般情況下,確立及謹守倫理或行為守則的確可以避免我們被自己從道德出發的選擇反噬。
最後,我還是希望我們能從上述好些例子中看到,道德與倫理之間(或者說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並非只能二選一,個人對政治人物誠信、對公義的追求還是非常重要:歷史上無數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吹哨人之所以可以為公共利益罔顧個人利益,憑的是道德勇氣;在國陣統治期間無數大馬人罔顧後果違法走上街頭,憑的亦是道德感召。很多時候後果的衡量亦視乎個人價值觀取向,是責任倫理觀難以解釋完全的(比如主張要在一定程度上維穩的人肯定覺得大混亂是要避免的後果,主張推進社會改革的人則認為維持現狀並非選擇,唯有衝撞才能鬆動結構,從歷史上看兩者都有一定道理,對錯要如何判斷?)。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把他提倡的正義論分成兩類,第一類理想理論(ideal theory)是奠基於理想的情況的應然理論,屬於最高標準,但在現實中一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會導致其無法支撐一個自由的制度,因此還需非理想理論(non-ideal theory)的指引,雖然理想理論該是大方向【註五】。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各族對各種問題的認知皆有落差,在倡導理想價值觀的同時,我們亦該意識到我們所處的環境並沒有那麼理想,進而避免只從道德觀點出發看問題,而是同時考慮到現實的局限、選項及各選項的好壞。如果經過這樣的思考過後還是選擇向良心負責或選擇向政治現實妥協,那才是真正負責和值得尊重的個人選擇,就如韋伯所說,才是一個真正成熟(mature)的人【註二】。
【註解】
一、利益申報:我在509大選時是反對馬哈迪任相但同意投票,現在立場相同。
二、Weber, Max (1919, 2004) Politics as Vocation. In the Vocation Lectures. Edited by Owen, David and Strong Tracy B and translated by Livingstone, Rodney.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三、「爲了從「正邪之爭」過渡到「好人分裂」,使多黨民主能够永續,我主張去道德化,而以倫理代替……」——見黃進發臉書,〈覆業華(二):信念倫理,責任倫理,馬哈迪,轉型正義〉(2020年5月26日)
四、Georgina Lee, Has Jeremy Corbyn ever voted with the Conservatives in Parliament?, Channel 4 News, 2018.09.04
五、Rawls, John (1971, 1999)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陳慧思 |
蘇格蘭阿伯甸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生,主要研究馬來西亞政治狀況如何影響其環境治理。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