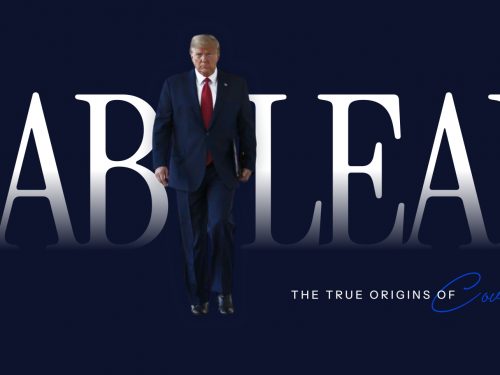(來源: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Malaysia/BERNAMA;有人出版社)
傳統出版媒介的生存空間遭受新媒介的鯨吞蠶食,知識生產與傳播科技改變了新世代的消費與閱讀習性,疫情只是加速了這個時代與世代的到來。馬華文學的「文學物流鏈」要怎麼以行動回應這個快速來臨的、紙本靈光消失的新紀元,有識之士不妨效法首相慕尤丁與其盟友,在移動管制的此時此地,以空間換取時間,思考應變良策,在後疫情時代精準地向前進擊,實現文學夢想。
【文/張錦忠】
過去一年多以來,馬來西亞社會歷經兩大變動。二〇一九年底,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開始蔓延,從中國、歐洲、東南亞、北美、澳洲、南美、到非洲,地球上的國家無一倖免,迄今全球確症病例仍然居高不下,疫苗開打了,但病毒也迅速變種,繼續蔓延;二〇一九年底以前的世界,已變成「美麗舊世界」。二〇二〇是張愛玲誕生一百週年,華人文化圈紛紛紀念這位五〇年代即移居美國的「祖師奶奶」,而《半生緣》末章曼楨那句名言——「世鈞,我們回不去了」,用來描述疫情時代對往昔舊時的懷念,格外貼切。是的,舊「世界,我們回不去了」。
但在東南亞洲的馬來西亞,早在二〇二〇年二月,時間早以斷裂,政府的政治結構已在一場「喜來登夜襲」行動中「被改變」——希望聯盟中有人在喜來登飯店夜會,圖謀拆解民選執政聯盟的組合,重新洗牌,另組新聯盟以取得政權。於是,人民票選上台二十二個月的希盟中央政府因首相馬哈迪辭職而告瓦解,各方勢力拉鋸,最後拜相的是慕尤丁,成立非經由普選產生的國盟政府,成功執政組閣。與此同時,冠狀病毒入侵,遍地散播,國家進入移動管制,政府擁有極大權力管制人民的行動與移動。疫情其實也是政治疫情,政府以對抗疫情之名,行自我賦權(「我們要當政府」)之實,今年更動用緊急狀態法令固權。
這是一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案例。人民在實體空間的移動與活動受限,彷彿時間行進的速度放緩放慢,但是政客取得更多進行利益交換的時間,讓搖搖欲墜的國盟政府苟延殘存。因此,說疫情救了倒塌中的政府並不為過。
馬華文學的生產環境以馬來西亞境內為主導,因此檢視一年多以來的馬華文學,有必要將馬華文學擺在疫情凌虐與政治危機下的存有空間,看看馬華文學的狀態。從這個角度檢視馬華文學,我們不妨重新思考「馬來西亞文學」與「馬華文學物流鏈」這兩個概念。
 (來源:Malaysia Gazette/Saharuddin Abdullah)
(來源:Malaysia Gazette/Saharuddin Abdullah)
沒有文化願景的新馬來西亞夢
贏得二〇一八年五月九日全國大選的希盟,不管當初多麼倉促成軍,還是包括了多元族群(公正黨、行動黨)、單一種族(當年的土團黨)、開明伊斯蘭(誠信黨)導向的成員黨,大體上呈現多元文化面貌,認可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也因此,儘管難免一廂情願之嫌,成員黨中有人以打造「新馬來西亞」自居。這樣的「新馬來西亞夢」,並非選後新猷,一九五七年獨立後的馬來亞、五一三事件以前的馬來西亞,人民大體上抱持這樣的共識──各族人民生活在一個兼容並蓄的國度,有所捍衛有所追求,不同的群體可以在各自的共同體自我實現小我大我,提出各種言論、主張與運動,表達苦悶與不滿,追求自由與幸福。
不過,希盟主政的那二十二個月,並未重啟國家文化或國家文學檔案,雖倡議新國家文化政策,卻沒有借助或落實文化的「軟力量」緩和種族關係張力,反而因爪夷書法納入小學課鋼、承認統考文憑等教育議題陷入泥沼,不見樹也不見林。回想希盟上台前高調提出選舉宣言《希望之書》,號稱「六十項承諾、百日十新政、五特別使命」,但裡頭並無任何文化愿景,當然,更沒有人談到「馬來西亞文學」。
在更遙遠時光隧道裡的一九六二年,新加坡國家語文發展局召開分馬來文、華文、英文、淡米爾文組別進行的「馬來亞作家會議」,討論「馬來亞文學」的形式與任務等問題,會中馬來作家要求大會決議「馬來亞文學須以馬來文書寫」,這項要求未被大會接納,結果提議者憤而退席,以示抗議。眾所週知,一九六二年會議沒有通過的提議,到了一九七一年的國家文化大會,就成為「國家文學」的規範了──只有以馬來文書寫的文學作品才有資格成為「國家文學」。其他語種的文學只能靠「邊」站,在馬來西亞文學複系統的邊陲運作。
 (來源:UM Memory)
(來源:UM Memory)
非馬來文書寫的邊陲命運
我沒有考證出席一九六二年「馬來亞作家會議」的馬來作家是否出席了近十年後召開的「國家文化大會」;但不管他們有沒有出席,文化大會關於文學的討論有點像當年會議的延長,而「國家文學須以馬來文書寫」的綱領就在大會拍板定案。此後五十年,馬華文學等其他語種的馬來西亞文學,未獲國家機器青睞,只能在國境內外自生自滅。希盟上台,還來不及做「新馬來西亞夢」就已瓦解,更不要說「我的文學夢」了。
疫情、疫情政治或政治疫情帶來的移動管制與緊急狀態,或許無關文學創作與文學夢想,但對文學通路的衝擊卻不容小覷。疫情開始,人民搶購的是民生用品,不是精神糧食。移動與封鎖管制禁止跨州出國,學校停停開開,人民移動力驟減,休閒娛樂餐飲等行業難免蕭條,書肆更受影響。換句話說,庶民的實體移動空間縮小,消費型態與規模不得不調整,製造業凍結聘僱或裁員,經濟必然受創,出版營運更不用說了。出版計畫不是夭折、延後就是縮小。例如,創立十八年的有人出版社過去一年來採精兵策略,迄今只推出五本書:黎紫書長篇小說《流俗地》、范俊奇散文集《鏤空與浮雕》、靈子散文集《曾經與你相遇》、冰谷散文集《斑鸠斑鸠咕噜噜》與海凡短篇集《野徑》,每本都擲地有聲。近年《星洲日報》的閱讀版每年推出「讀家年度選書」,去年底的二〇二〇文學類選書雖然選出了十本,但編者也說受疫情肆虐影響,「書量明顯比往年少」。
在苦悶的年代,作家可能依然吶喊與反抗,創作不懈,出版品卻需要通路與物流,在移動管制的時空,書店與出版社首當其衝,買書的人更少了;買書人少,書店與出版社的現金流量出入失衡,週轉不靈,就很難撐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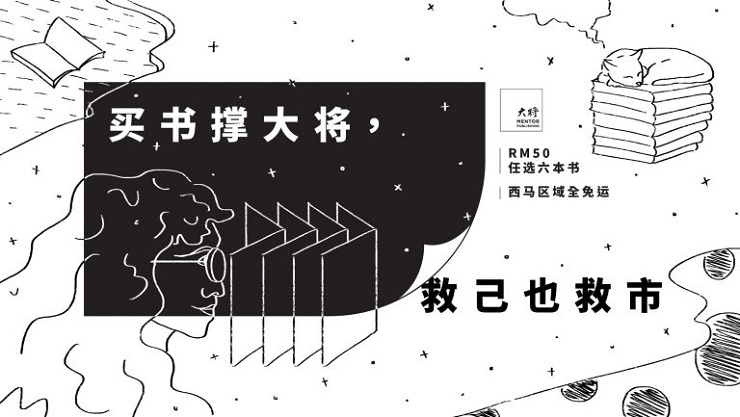 (來源:大將出版社)
(來源:大將出版社)
疫情衝擊書店出版社
於是,我們看到大將出版社在二〇二〇年九月底發起「買書撐大將,救己也救市」活動,期待有五千人每人掏出五十令吉買六本書,反應相當熱烈,很快就超標。不過,低價優惠募資,顯然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渡過一關之後,遇到下一關就不太可能複製了。繼大將出版社之後,紅蜻蜓出版社、文運書坊(Gerakbudaya)也發出財務面臨虧損的訊號,呼籲支持者幫撐相挺。這並不是骨牌效應,而是市場機制問題──傳統出版媒介的生存空間遭受新媒介的鯨吞蠶食,知識生產與傳播科技改變了新世代的消費與閱讀習性。
大將、紅蜻蜓、文運都是經營了二十年的出版品牌,書系路線㢠異,讀者分屬不同受眾,除非投資評估錯誤,否則即使獲利不高,應該可以持穩營運,疫情與移動管制固然讓平常就不怎麼景氣的書肆行情雪上加霜,但不是書肆萎縮的唯一因素。(記得許多年前臺灣出版界一直在喊那隻叫「大崩盤」的狼來了,喊了很多年,現在狼終於在遠處前方向我們奔躍而來了,只是還沒有來到我們眼前罷了。)
其實,那不是一匹狼。那是一個新媒介時代的來臨,疫情只是加速了這個時代與世代的到來。馬華文學的「文學物流鏈」(我稱之為「物流鏈」,其實就是產業鏈)要怎麼以行動回應這個快速來臨的、紙本靈光消失的新紀元,有識之士不妨效法首相慕尤丁與他的盟友,在移動管制的此時此地,以空間換取時間,思考應變良策,在後疫情時代精準地向前進擊,實現文學夢想。
 張錦忠 |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目前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華語語系文學。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