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Fareez Fadzil )
今時今日的馬來西亞是前面半個世紀不同社群、利益關係者互動的結果,包括華裔與印裔社群如何回應巫統,以及國陣的文化霸權與種族中心主義政策。各族群內部為了團結以對抗外來威脅,皆以犧牲內部多元差異為策略,都以如何與對方區隔,來界定自己的身份。半世紀以來初次政黨輪替,理想的馬來西亞,不可能一蹴可幾,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更持平的去省視,去理解歷史的發生,思考如何公平地呈現過去大時代給每一個人帶來的傷痕。
【文/黃書琪】
新馬來西亞(Malaysia Baru)不是希盟政府率先丟出來的論述,是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自發於民間與支持者的口號,隨後被廣泛使用。無論如何,新馬來西亞不能只是一個口號,馬來西亞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有了重生的機會,那麼,我們想像的馬來西亞,究竟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才是必須討論的問題。
弔詭的是,新馬來西亞誕生在一個全球認同政治抬頭的年代。在認同政治席捲美國、歐洲乃至於亞洲國家,排外、種族主義在各地抬頭之際,被《血路盛世:當代東南亞的權力與衝突》(Blood and Silk: Power and Conflict in Moder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麥克.瓦提裘提斯(Michael R.J. Vatikiotis)直接標籤太過種族主義,讓他受不了而離開的馬來西亞,卻打破了過去半個世紀族群政治為政黨輪替設下的門檻限制,迎來首次政黨輪替。如果說,這是奇蹟,似乎也不為過。
可是,舊馬來西亞並沒有立即消亡,包括這個年代全球認同政治所牽動的每一個個體的行動,都在影響新馬來西亞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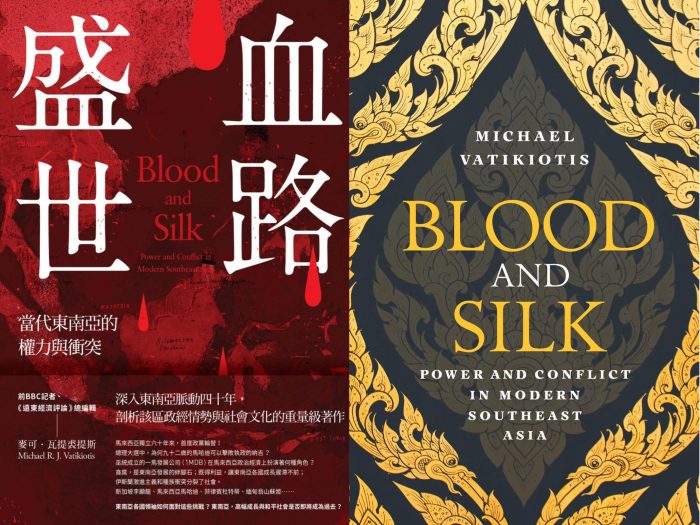
那什麼是新馬來西亞?所謂新,是否只是對照於舊的存在?
與其用新舊來區隔,借用舊的來定義新的,我更希望,這一代的馬來西亞人思考我們要的馬來西亞究竟長什麼樣?如果說過去半個世紀的馬來西亞沒有長成我們要的樣子,那現在就是重新定義何謂馬來西亞的時候。
文化霸權與文化民主交鋒
1968年,兩個當時都是在野黨的多元族群政黨在吉隆坡人民信託局(Malaysia’s Majlis Amanah Rakyat ,MARA)禮堂針對馬來西亞文化展開激辯,那就是民政黨和民主行動黨的文化大辯論。
辯論的導火線是民政黨黨員賽納吉(Syed Naguib al-Attas)在1968年7月11日一場座談會提出,馬來西亞文學是透過馬來文書寫的文學,因此,包括印尼人書寫的文學作品,也可以算在馬來西亞文學範疇之內;相反的,只要不是馬來文書寫,儘管是馬來西亞人創作有關馬來西亞這塊土地的文學作品,都不能算是馬來西亞文學。
這個立場引起林吉祥的注意與回應,接著下來就是轟動一時的文化大辯論。林吉祥認為馬來語是國語沒錯,但並不表示其他馬來西亞人使用的語言不「馬來西亞」。【註一】賽納吉和他的辯論於是成為所謂文化霸權與文化民主的交鋒。
賽納吉雖然身在當時還是在野黨的民政黨,但他的立場多少反映了當時已是執政黨的聯盟的態度。1969年後,民政黨加入國陣,賽納吉說法背後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或譯民族優越感)與文化霸權當然也牽動了日後整個馬來西亞社會不同社群的反應。
今時今日的馬來西亞是前面半個世紀不同社群、利益關係者互動的結果,包括華裔與印裔社群如何回應巫統,以及國陣的文化霸權與種族中心主義政策。
例如說《拉曼達立報告書》(Rahman Talib Report,1960)催生了華文獨立中學,如果沒有收編、取消津貼等問題,獨中可能不會存在,也不會有七十年代才出現的獨中統一考試文憑(統考)。
犧牲內部多元差異代價沉重
政府由上而下強壓以強化馬來語文在各個公共層面的地位,華人社會對抗馬來文化霸權的反應則是團結統一以禦敵。當馬來社會獨尊馬來語文為民族語文,地方方言如吉蘭丹土話與地方文化一一面對威脅;同樣的,華社要確保馬來西亞華裔獨尊華語文,義對抗日益強大的馬來文化霸權,第一個受害者也是方言。
我來自不必罰款因為早已沒有人在學校講方言,這個遭新加坡講華語運動同化的大新山地區,長大了才知道原來中北馬獨中把講方言當作禁忌。我的年代,會講方言的同學出外籌款,應對老人家說起潮州、福建話才方便,而我已經喪失了講方言的能力。
 (來源:光明日報)
(來源:光明日報)
更有趣的案例是《四喜臨門》(上圖),這齣處境喜劇於五十年代起初以廣播劇形式風靡華社,六十年代國家廣播電視臺成立後,進軍電視螢幕,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才停播。劇中由四個演員以四種方言(福建、客家、高州、粵語)夾雜華語、馬來語,把馬來西亞人日常生活搬上螢幕,貫徹馬來西亞人精神。可是,隨著1979年新加坡政府極力推動講華語運動,八十年代開始,馬來西亞華社也提倡講華語運動,國家廣播電視臺最終在1988年宣佈停播《四喜臨門》,其中一個原因即是民間華團反對。【註二】
三十多年後,當民間有人推動鄉音運動,汲汲營營保存方言文化,回看歷史,不禁感嘆華社上個世紀對抗馬來文化霸權採取的策略付出了多麼慘痛的代價。
馬來社會官方獨尊正統馬來與伊斯蘭文化,許多傳統馬來文化(如皮影戲和騎馬舞)面對與華人方言相同的困境,其代價與我們正在快速流失的方言一樣慘重。
各族群內部為了團結以對抗外來威脅,皆以犧牲內部多元差異為策略,因為大家都以如何與對方區隔,來界定自己的身份。也就不怪乎吃豬肉、賭博、喝酒等穆斯林引以為戒的習慣,成為非穆斯林界定自己身份的象徵。
來到2018年的今天,我們是否能夠至少得出一個結論,上個世紀的做法不一定值得推崇,我們可否找出一個包容差異、鼓勵多元,各種文化共存共榮、互相輝映的馬來西亞文化?
馬來西亞文化肯定不能只是多元的大雜燴,我們必須叩問,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如何與印尼的馬來人不同,馬來西亞的華人如何與東北亞甚至其他國家的華人不同,馬來西亞的印度人如何與南亞次大陸的印度人不同一一這些「不同」就是我們內在的馬來西亞,構成我們馬來西亞人的部份。
這個馬來西亞的部份有令人愉悅的,也當然有不怎麼討喜的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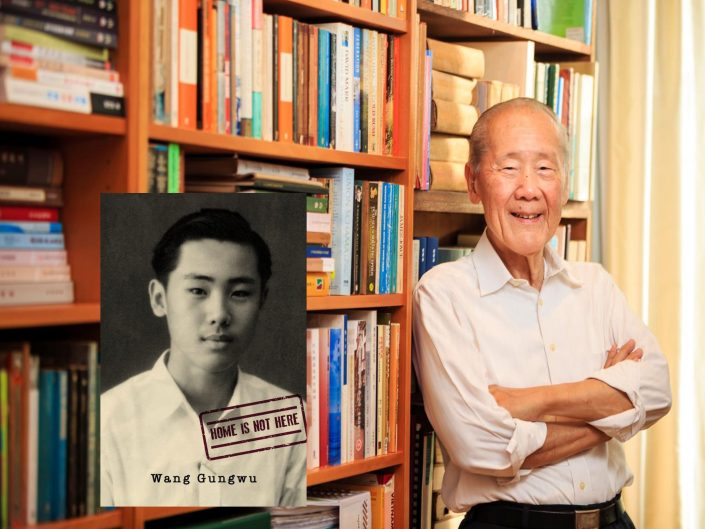 (來源:NUS Press;Lingnan University)
(來源:NUS Press;Lingnan University)
王庚武在敘述早年經驗的自傳(只談到幼年及進入馬來亞大學時期),用了「Home is not here」為題,直白理解是指父母親一直告訴年幼的他,家鄉在遠方,不是腳下的南洋;更可能隱喻的指涉回到中國後才發現家鄉在南洋,不在從小魂縈夢繫的中國。他的自傳與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A Memoir,中國譯為《格格不入》)同樣叩問個人的身份與認同。
他的馬來亞人的部份,是語言、味覺(乃至於喜歡吃什麼、不能消化什麼)、以及許多個人生活經驗堆砌出來的印記。
省視時代背後的血淚傷痕
這些個人記憶,包括對上個世紀影響建國的種種歷史,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更持平的去省視,去理解歷史的發生,思考如何公平地呈現大時代給每一個人帶來的傷痕。
例如我母親家庭的遠方親戚曾經派駐彭亨州黑區的政治部,半個世紀後,當我問起對馬來亞共產黨的看法,他依然毫不思索地說絕不原諒他們,因為他的兄長就死在馬共槍下。弔詭的是,我父親的親戚裡卻有共產主義的同情者,雖然出生、成長在馬來亞,卻毅然決然回到五十年代的新中國,經歷文化大革命,幾十年後當我問起那時的狀況,老人家只是很淡然地說,沒什麼,沒什麼。
我可以理解前者的恨,在戰爭裡對錯不是那麼直接,更直接的是生與死,面對摯愛的生死,有多少人可以做理性選擇?而後者在離鄉半個世紀後,無法忘懷的是幼時嚐過的榴槤,南洋的味覺像是銘刻一般,從來沒有離開他的舌頭,後輩如我只能在他每次返鄉,到處買榴槤,滿足老人家半個世紀無法滿足的鄉愁。
 (來源:Youtube)
(來源:Youtube)
這些歷史的傷痕,刻在大時代底下每一個個體的生命裡。半世紀以來初次政黨輪替,許多人無不希望很快為過去本身不被承認、受冤屈、抹煞掉的生命找到出口,出現一個大家殷切盼望的馬來西亞。
這個理想的馬來西亞,不可能一蹴可幾,我們要清理創傷,要看到彼此共同經歷的傷痕,承認大時代下的個人,不一定如精英階級有逃避的選擇,例如被馬共殺掉的馬來警察。
下一步,則是定義我們的馬來西亞。這篇文章並沒有要明確定義何謂「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必須由這一代人去重新建構,我們做什麼,我們如何對應其他社群改採取的行動,將會決定半個世紀後的馬來西亞長什麼樣。我只期待,我們不再重蹈覆轍。
【註解】
一、Ooi Kee Beng,Lim Kit Siang:Defying the Odds,Singapore: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Pte Ltd,2015。
二、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臺灣:聯經,2018。
 黃書琪 |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公共行政碩士,馬來西亞柔佛州居鑾區國會議員,曾任記者,現為全職政治工作者。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