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Education Week)
如果我們是基於優先性的概念去糾正社會的不平等問題,那麼我們就有更好的理由採用提昇劣勢群體的策略,而不是降低優勢群體的策略。就此而言,用優先性概念比用平等概念來理解〈第153條文〉,更為恰當。因為在獨立前後的現實狀況中,人們有可能都會同意,優先提昇劣勢群體的水平是首要任務,藉以糾正當時社會之中的不平等現象。而如今,相同問題的討論幾乎是圍繞在經驗性的分析,以闡明既有的狀況。相反的,在概念上的分析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釐清問題背後的意涵,以及各種可能的預設與蘊涵。
【文/陳鳴諍】
「平等(equality)」被認為是一個普世價值,也是人類社會應該追求和捍衛的。在民主國家裡,平等作為一項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而被寫入國家的憲法裡。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制度與行為規範都離不開平等概念,成為我們追求福幸生活的基礎之一。
概念上,平等是抽象的,因為我們無法在人類所及的經驗範圍內,觀察到「平等」。相反的,經驗帶給我們的是各式各樣的差異,社會中充斥著各種現實差距:性別與膚色的差異、能力才智的差距、財富資源的差距等。在政治哲學裡,學者想要論證,有些差異與差距並非都是自然的,而是具有規範性的意涵,同時找出一個有效的方法來達至平等。
如果我們接受平等作為一個普世價值,我們會把任何涉及平等與不平等的事物看成是很自然的。我們可以談論社會平等(social equality)、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法律平等(legal equality)、經濟平等(economic equality)。但是,人們總是被各種各樣的差異所包圍著,排除這些差異需要藉助抽象的能力。少了這種抽象能力,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人類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如何說服人們跳脫這些差異,去接受一個抽象的平等概念,是非常困難的。
 (來源:Shutterstock/UNtoday)
(來源:Shutterstock/UNtoday)
概念上,我們可以區分出平等的兩種不同意涵。在第一種意涵下,平等是抽離了一切差異,只關注人們內在共同的部分。有些哲學家認為,就內在性而言,每個人都擁有理性能力(rationality)與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縱使每個人在性別、膚色、宗教、文化、能力、財富與社會地位等存在著差異,但是理性能力與人性尊嚴卻是每個人都共有的部分。就此而言,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也應該平等地被對待。
抽象能力讓我們在各種不同差異的背後看到共同性。缺少了這種抽象能力,我們會被現實中的各種差異所蒙蔽。這些差異讓我們以為,我們在某方面比其他人來得更加優越,並且享有特定的權利與優勢,其他人則不是。這也意謂著,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必須在排除與不考慮各種差異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被思考。
但是,現實生活中僅有這種意涵的平等是不夠的。主張每個人都是(is)平等的,這可以是一種描述性主張(descriptive claim);而主張每個人都應該(ought to be)是平等的,卻又是另一回事,這是對事態的一種規範性主張(prescriptive claim)。
 (來源:FDR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Wikipedia)
(來源:FDR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Wikipedia)
誠然,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各種先天的和人為的差異與差距,有些被認為是可被接受的,有些被認為是不可被接受的。有些差異是天賦本然的,例如:性別、智力、才能等等。對於這些,縱使我們說它們是不平等的,但是這種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有些差異卻是人為所致的,例如權利、社會資源的分配等。對於這些,我們會說它們是不平等的,而且是無法被接受的。
人類社會嘗試透過一些方式去糾正各種可能的不平等現象。因此,我們還需要有規範性意涵的平等,以特定的方式減少現實中不平等的現象。這種規範性意涵的平等就是糾正社會之中的各種不平等、不可接受的現象。
於是乎,我們會看到一種主張:由於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我們應該致力於消除社會中各種不平等的問題。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開宗明義就主張:由於每一個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因此我們應該反對英殖民政府所施加的一切不公不義。二十世紀的聯合國《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也主張,每個人在尊嚴與權利上都是平等的,因而每個人都應該免除於各種歧視與不公所帶來的傷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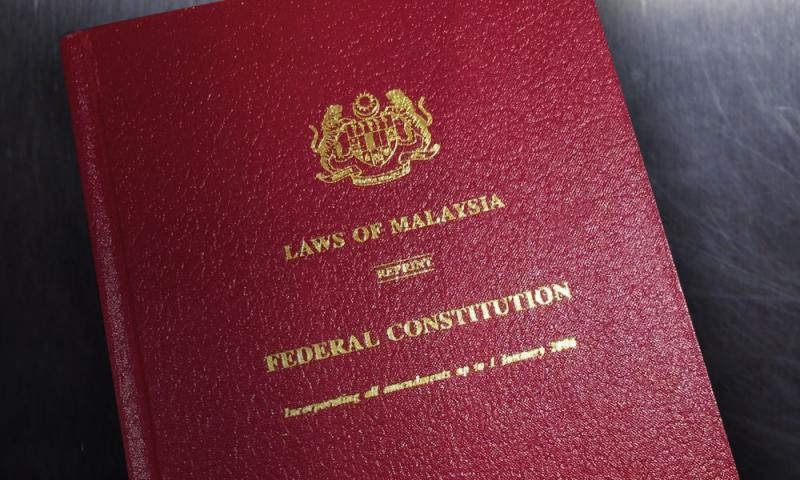 (來源:Malaysiakini)
(來源:Malaysiakini)
事實上,這樣的主張包含了上述兩種不同意涵的平等概念。當我們主張人人平等時,它一方面指的是在不考慮任何既有的差異之下,並且就人的理性與尊嚴而言,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具有等同的地位。另一方面,就社會的現實層面存在各種可能的不平等,如果這樣的不平等是後天人為所致的,那麼我們就有義務去糾正這樣的不平等。
對於這兩種不同意涵的平等的結合,我們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認為糾正不平等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我們責無旁貸,而這種道德要求正是基於我們對於平等概念本身的理解。我們幾乎不會去質疑,從描述意涵的平等概念過渡到規範意涵的平等概念,在邏輯上是順理成章的。從前者過渡到後者的邏輯關係是否成立?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裡不進一步追究。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也闡明了這樣的平等精神。《聯邦憲法》的第8條所闡明每個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這樣的平等概念正是抽離了既有的各種差異後,才能得以被突顯出來。同時,該條文也闡明,每個人都不應該因為其種族、宗教、性別等等的因素而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亦即,遭受到歧視)。這種規範上的要求也蘊含著,徜若社會中存在著不平等的對待,我們必須馬上給與糾正。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爭論《聯邦憲法》中的〈第153條文〉的內容。該條文闡明馬來人的「特殊地位(special position)」,既有的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政策都離不開這條文。這條文是否違反了〈第8條文〉所闡明的平等精神?如果我們用平等概念來檢視,〈第153條文〉顯然與〈第8條文〉相衝突。因為〈第8條文〉要求我們摒除各種既有的差異,而〈第153條文〉卻是以種族的差異作為前提。
對一個政府而言,如果平權行動在既有的憲法框架能夠得到證成(基於平等概念),而其所產生的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又不與憲法產生衝突,那麼這一切自然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我們很難不懷疑是否能做到這樣的地步。
倘若如此,我們只能在法律領域之外的道德領域,尋找理由去證明,為了糾正社會中更嚴重的歧視與不平等,逆向歧視是被允許的。如果我們不用平等概念來檢視,這樣的衝突就不一定會出現。但是,我們有可能不用平等概念來檢視〈第153條文〉嗎?
英國哲學家Derek Parfit(1942—2017)主張,我們常會混淆了「平等」與「優先性(priority)」兩個概念,我們應該區分兩者的不同。在一些情況下,我們是基於平等的概念去糾正不平等的現象,而且這個不平等本身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在一些情況下,我們會糾正不平等的現象,並不是基於平等概念,而是基於優先性的概念。
Parfit給出了一個簡單且符合道德直覺的解釋。如果是基於平等概念而去糾正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我們可以有兩種作法:第一,想方設法幫助處於劣勢的群體,使他們的處境能夠提昇(levelling up)到另一組處於優勢的群體的水平;第二,想方設法讓處於優勢的群體降低(levelling down)至劣勢群體的水平。由於這兩種結果都是平等的,所以都是可以行的,也就無法說明何者孰優。
但是,如果我們是基於優先性的概念去糾正社會的不平等問題,那麼我們就有更好的理由採用提昇劣勢群體的策略,而不是降低優勢群體的策略。就此而言,用優先性概念比用平等概念來理解〈第153條文〉,更為恰當。因為在獨立前後的現實狀況中,人們有可能都會同意,優先提昇劣勢群體的水平是首要任務,藉以糾正當時社會之中的不平等現象。
而如今,相同問題的討論幾乎是圍繞在經驗性的分析,以闡明既有的狀況。相反的,在概念上的分析也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釐清問題背後的意涵,以及各種可能的預設與蘊涵。
 陳鳴諍 |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按贊和追踪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來源:
(來源: (來源:
(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