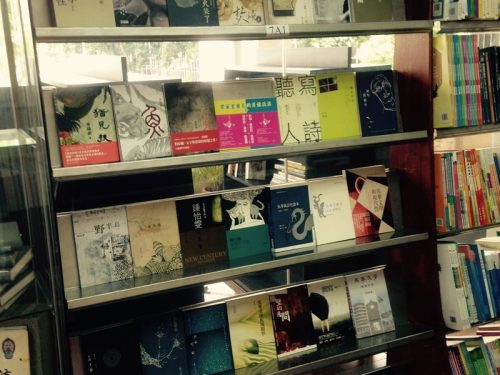(來源:Malaysia Gazette/Affan Fauzi)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族女子學校提供的現代民族教育,除了注重現代知識的裝備,也著重培養民族意識。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新一代,惟對傳統缺乏反省。直至今日,馬來西亞的學校仍然如此自我定位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搖籃,實際上可能已壓抑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族群內部較弱勢者的權益。換言之,在建構身份認同上,長期的正規教育和社群精英論述,可能比個人切身受歧視的經歷更有影響力。因此,張美嫻的結論——族群意識對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力遠遠強於性別意識,雖源自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女子教育之研究,用來理解現今社會仍然充滿洞察力。
【文/吳益婷】
馬來西亞以族群爲基調的政策,影響了每個國民的際遇,族群政治一直是馬來西亞政治最顯著的特徵。但這些政策存在的性別歧視,似乎很少成爲話題,也不如族群政治般能激起廣泛議論。首相慕尤丁日前宣布防疫期間的振興經濟方案時,曾以Makcik Kiah(吉雅阿姨)的代稱來說明低收入群體(B40)將如何受惠,其中月入低於四千令吉的家庭可获一千六百令吉援助金。那到底哪位家庭成員可享有呢?是Makcik Kiah本人嗎?根據稅務局常見問題的答案,若夫妻兩人分別報稅,上述援助金將存入當局眼中一家之主的銀行帳戶,亦即Makcik Kiah該戶的一家之主。依據慣例,在傳統父權社會,一家之主是Makcik Kiah的丈夫。即便丈夫已經退休,她仍在工作養家,仍然不是一家之主。
如果這種差異導致是族群性的,我相信會刺痛比較多人。公民社會組織很多依據種族族群平等、文化表述的空間主體,只有少數處理性別歧視,也很少有意圖推動性別平等。因此,性別平等和消除政策上的歧視訴求很難進入主流論述。在一些情況下,性別歧視甚至成為一種不痛不癢的常態。
在這段無法自由出門的日子,我細讀了一本考察馬來亞和新加坡女子學校的教育歷史的著作——《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暫譯:學校流散者: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女性、教育和海外華人,1850至1960年代】(紐約:牛津出版社,2018)。作者是目前在美國石山大學執教的歷史學者張美嫻(Karen Teoh May-Shen)。本書以女子學校及其華裔畢業生為個案,梳理女子學校的教育史,不過,並未局限於性別和學校教育,也討論「海外華人」在英殖民政府管制下的文化選擇和社會領袖的性別視角。該研究發現,許多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華裔女性,族群身份的認同遠強於性別意識。
本書詳細介紹兩種類型的女子學校的建立動機和後來的發展,一種是西方傳教士所設立,目的是慈善、教育和傳教;華校則是民族自強,提倡現代教育,促進華人女性的水平。當然教會或華社領袖創辦的女子學校,都有父權的視角和期待。
從今天來看,昔日的父權觀念是保守且具優越感,在當時卻是進步的。對華社領袖而言,他們自視爲民族領袖,且意識到女性是民族的重要成員,因此要爲女性提供現代化的教育,達到民族自强和現代化目的。但不少女子學校畢業生發現,自身家庭和社會無法像學校那樣接受她們的新角色。雖然如此,她們並未因此投入女性醒覺運動,那個年代,特別是華校畢業生更傾向於獻身民族解放運動,包括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參與民族國家的成立等。
從正面來看,學校可以平等地對待學生,不論男女都讓他們對社會和國家有共同的認識機會,賦予相等的責任,對很多女性和弱勢群體是一項賦權經驗——即可與過去享有特權的群體(如男性受教育者)一起參與公共生活,體驗超越自我和家庭,參與國家建設的成就感。
 (來源: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來源: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然而,民族教育倾向漠視內部成員的權力和資源不平等結構,接受傳統社會結構的歧視,甚至視之爲可接受的常態。民族領袖往往是這些傳統社會結構的優勢者,如果沒有民族「外敵」,他們不會傾向重組社會結構。過去,真正能挑戰民族內傳統勢力是階級革命,但這樣的運動在二十一世紀幾乎已經銷聲匿跡。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族女子學校提供的現代民族教育,除了注重現代知識的裝備,也著重培養民族意識。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新一代,惟對傳統缺乏反省,尤其是「尊卑」的社會關係——長幼、性別和君臣等關係。直至今日,馬來西亞的學校仍然如此自我定位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搖籃,實際上可能已壓抑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族群內部較弱勢者的權益。
譬如,即便一些女性在她們成長的社會,包括受教育機會,市場差別待遇,家庭地位、財産分配等,也是明顯被歧視的。當中承受的某些傷害甚至是暴力的,如家暴,强暴等,是高度性別的。這些來自日常、傳承,甚至會發生在她們女兒身上的差別待遇,也極少激起對既存制度的憤慨。換言之,在建構身份認同上,長期的正規教育和社群精英論述,可能比個人切身受歧視的經歷更有影響力。所以,張美嫻的結論——族群意識對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力遠遠強於性別意識,雖源自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女子教育之研究,用來理解現今社會仍然充滿洞察力。
 吳益婷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研究領域為砂拉越政治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來源: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