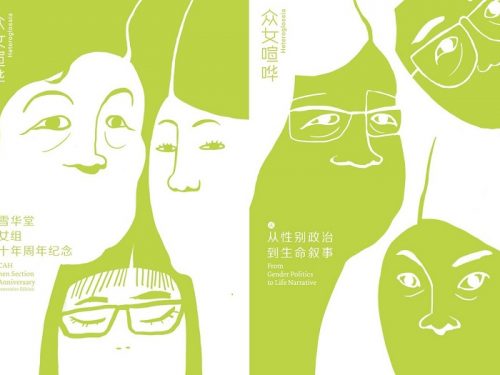(來源:Epicure & Culture)
亞參叻沙為我們描繪出的滋味地圖,這層次豐富的混雜味道,依附在檳城發展的地緣脈絡之上。從英屬東印度公司時代開始,直至二戰之前,英國人對檳城的統治相對寬鬆自由,在移民政策方面尤為放任,幾乎沒有什麼特別限制。因此,各族群都能夠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檳城繁衍,多元的族群人口結構也得以長期維繫。不僅如此,在檳島中心地帶,早年曾長期維持族群階層雜居的局面。時間與空間留給檳城獨特的斑駁色彩,深藏在每一口層次豐富的娘惹美食裡,可堪玩味。
【文/閻靖靖】
到過檳城覓食的遊客,想必不會錯過亞參叻沙(Assam Laksa)。與檳城蝦麵齊名,亞參叻沙也是本地獨特的娘惹料理。而且,人們在提到它的時候,總會特別強調它與南馬、星洲的Laksa不同;檳城本地人更會略帶不屑地說,南部那種Laksa只是「咖喱麵」——因為在檳城人的字典裡,Laksa是專指Assam Laksa。
那麼,一碗亞參叻沙,藏了多少檳城娘惹美食的密碼?許多遊記、美食推介或學術文章都曾提及,在三州府都有的峇峇娘惹傳統裡,檳城娘惹烹飪的食物,與馬六甲、新加坡的風味頗不相同。但是細究其差異,卻又常常只是含糊其辭地說,檳城娘惹菜兼具泰國及南印度的烹飪元素——至於是哪些元素,則多語焉不詳,更鮮有探究這些差異的由來。人類學家陳志明曾將星馬娘惹飲食大分二類,即以檳城為代表的北部娘惹傳統,和以馬六甲、新加坡為代表的南部娘惹傳統。不過陳氏強調的,多是相近而非相異之處,討論的焦點也在馬六甲和新加坡,檳城方面著墨不多。
讓我們先從這碗亞參叻沙入手,看看究竟有哪些週邊民族的烹飪元素滲透其中。
先說魚湯。熬製湯頭常用的魚肉,來自Ikan Pupu、Ikan Parang(Wolf-herring)、Ikan Kembong(Mackeral)、Ikan Terubuk(Shad)及細骨較多的 Kembong(Chubb Mackeral)——這些魚都有確切的馬來文名稱,當可推測是從本地馬來人常吃的魚類中借鑑而來。 採用叻沙葉及其他濃厚香料熬製湯頭,再配以粉麵,稱之為Laksa,也是馬來人常吃的風味。
各族烹飪元素風味混雜
再說湯裡的酸味。那主要是「亞參片」和「亞參膏」的滋味。二者皆酸,但卻來自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亞參片」極酸,而「亞參膏」則是酸中帶甜。亞參果(asam gelugur / asam keping)學名Garcinia Atroviridis,是一種原產馬來半島的高大喬木所結的果實,在北馬泰南都很常見。它的果肉切片、曬乾,擺在巴剎裡,名為「亞參片」——許多人將這種黑褐皺縮的乾果肉誤認為是羅望子(Tamarind,學名Tamarindus Indica),網絡上不少文章都以訛傳訛。
其實,黏稠膏狀的「亞參膏」才是來自羅望子。它是用羅望子豆莢狀果殼內的果瓤和種子製成。這種熱帶植物原產東非,在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度等邦廣泛分佈,不僅是南印度烹飪常用的酸味調料,在許多地方還有甜味的品種,可以直接當水果食用。另外,羅望子在中國西南也用於烹飪,名為「酸角」或「酸豆」,取其「酸味豆角狀」之意。以「亞參膏」為主要調料烹飪而成的「亞參蝦」,亦是一款典型的檳城娘惹海鮮。 除了香辣,酸味在檳城娘惹食物中也十分常見。
扯遠了,説回亞參叻沙。一碗合格的亞參叻沙,必不能少了一匙濃黑的蝦膏。這也不是常見的磚塊蝦醬峇拉盞(Belacan),而是用蝦頭內的「蝦黃」熬成的醬汁,鮮甜濃郁,略帶腥氣。正是這腥甜的蝦膏,令亞參叻沙一試難忘——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濃厚的滋味!同樣少不了這蝦膏的,還有檳城羅惹(Rojak)。據說這種蝦膏在印尼也有製售。
上菜之前,還要加些點綴:一團切成細條的鳳梨肉、萵苣葉、叻沙花,再加幾片薄荷葉。這種大量新鮮香草蔬果入饌的手法,頗不同於島嶼東南亞將香辣料悉數搗爛做成Rempah的傳統,顯然是受以泰越料理為代表的烹飪風格影響。
最後,湯裡浸泡著長軟又彈牙的米線,這既是來自中國原鄉的飲食傳統,又早與馬來社會交融。整碗亞參叻沙裡,也就只有這款麵底,還嚐得出華人食物的特點。除此之外,我們品嚐到本地盛產的魚肉、亞參果、南薑、香茅、叻沙葉、紅蔥頭,以及來自東非和南印度的羅望子、與印尼頗有淵源的蝦膏、泰越風情的新鮮香草蔬果,當然還有歐洲人從美洲引進的辣椒。這已經幾乎畫出了大半張世界地圖。顯然,除了受泰國與南印度烹飪影響外,檳城娘惹菜還有更多元的影響源頭,而「風味混雜」往往也是它給訪客留下的深刻印象。
正如亞參叻沙為我們描繪出的滋味地圖,這層次豐富的混雜味道,的確依附在檳城發展的地緣脈絡之上。
地緣脈絡描繪滋味地圖
檳城位處馬六甲海峽北端,向西北方望去,依次是安達曼海、孟加拉灣與南亞次大陸。雖然今天它是一個東南亞都市,但是讓這個港口與世界相連的海洋,幾乎全都屬於印度文化圈。無怪乎開埠初期,檳城曾被描繪為一個「印度的港口」。1826至1830年,檳城曾經短暫作為三個海峽殖民地的首府。而當時的三州府隸屬英屬印度的首都加爾各答。1857年,當新加坡力爭讓海峽殖民地脫離印度管轄、轉由倫敦直轄的時候,檳城方面對此事並不熱心。檳城與印度這層微妙關係,從側面印證了印度帶給檳城的影響,遠甚於它在甲、新兩地留下的印記。
 (來源:Penang Time Tunnel)
(來源:Penang Time Tunnel)
因為處在東南亞與南亞的交界位置,檳城開埠不久,就已是極重要的轉口貿易港。1868 至 1890 年間,暹羅和緬甸都是檳城在東南亞的主要市場。同時,檳城與英屬印度各港口之間的貿易聯繫也很緊密。此外,連通亞歐大陸的現代蘇伊士運河於 1869 年開通。這件遠在千里之外的事,也直接影響到檳城。向東行駛的歐洲商船不再需要繞行非洲南端,他們經過南亞之後,遇到的第一個重要港口就是檳城。一些新的蒸汽船公司因而選擇此處作為它們的營運基地,這讓檳城的區域貿易樞紐地位愈發重要。
頻密的商賈往來,自然帶來更多層面的交流。二十世紀早期,檳城還是區域教育樞紐。這裏不僅有現代伊斯蘭教育的先驅機構Madrasah al-Mashoor al-Islamiyah,還有眾多優良的英校與華校。不同族群、語言、宗教的學生們,廣泛來自馬來半島、老挝、柬埔寨、泰國、汶萊、菲律賓、印尼甚至印度。同時,還有許多來自泰南與蘇門答臘的穆斯林,停留在檳城等待季候風,前往麥加朝聖。
此外,從英屬東印度公司時代開始,直至二戰之前,英國人對檳城的統治相對寬鬆自由,在移民政策方面尤為放任,幾乎沒有什麼特別限制。因此,各族群都能夠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檳城繁衍,多元的族群人口結構也得以長期維繫。
不僅如此,在檳島中心地帶,早年曾長期維持族群階層雜居的局面。今天喬治市不同族群、宗教的古建築比鄰而居,便是這段歷史在城市空間格局留下的痕跡。相較而言,馬六甲老城區主要是華人聚居,馬來人則住在週邊的農耕地區;而在新加坡,開埠初期就已有明確的族群社區劃分,不同族群的生活空間也較少交錯。
除了亞參叻沙,還有許多可以細究的個案:海南豬肉沙爹,經海南籍新客廚師在英國僱主的廚房裡改良,不僅選用華人最常吃的肉類,與馬來—印尼傳統的沙爹烤串混搭,蘸醬也改用羅望子和來自新大陸的蕃薯,而不是椰漿與花生。連佐餐的Ketupat,亦換成英人更慣食用的切塊烤麵包。檳城Otak也不同於麻坡Otak,不採碳烤而用蒸炊,蕉葉摺成別緻的「鯉魚包」,則顯然與泰國的Hor Mok Pla(蒸魚咖喱)系出同源。時間與空間留給檳城獨特的斑駁色彩,深藏在每一口層次豐富的娘惹美食裡,可堪玩味。
至於檳城娘惹風味如何走出神秘的娘惹廚房,以遍地開花的姿態將檳城打造成「美食之都」?我下次將另文撰述。
【延伸閱讀】
Tan, Chee-Beng. 2007. Nyonya Cuisine: Chinese, Non-Chinese and the Making of a Famous Cuisine in Southeastern Asia, in Sidney C.H. Cheung & Tan Chee-Beng (eds.), Food and Foodways in Asia: Resource, Tradition and Cooking, pp.171-82. London: Routledge.
Yeoh, Seng Guan et al. (eds.) 2009. Penang and Its Region: The Story of an Asian Entrepôt, pp.7-29. Singapore: NUS Press.
閻靖靖、王國璋。2016。〈走出娘惹廚房:初探檳城華人飲食文化蛻變〉,發表於「地方與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飲食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2016年10月28-29日,中國廣州中山大學 。(主辦: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
 閻靖靖 |
文字及漫畫作者,同時是個陪倆孩子玩得不亦樂乎的媽。研究興趣包括全球化與華人移民、城市網絡、文化產業、新媒體發展等。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來源: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