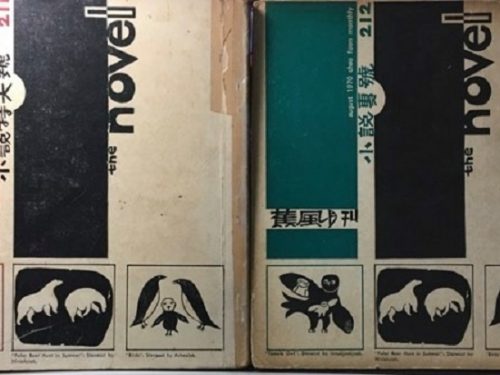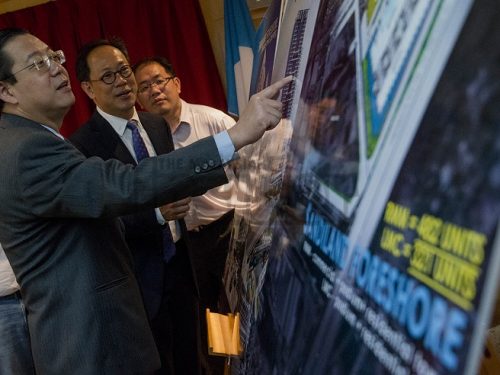(來源:MalaysiaNow/Djohan Shahrin)
體制慣性導致無論大馬計劃、財案或政策思維,只能夠年復一年延續、強化既有的發展與分配模式。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甚而使馬來西亞成為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當經濟發展弱化至分配出問題時,只能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把問題踢給其他部門,或把預算案隱藏在預算外繼續歌舞昇平。2022年財案缺少的,恰恰也是過去三十年所失去的。諸如此類的財案一再提呈,但世界不會再等待馬來西亞。
【文/李健聰】
截至今日,財政部長東姑扎夫魯(Tengku Zafrul Aziz,上圖)尚未解釋他之前的境外帳戶,卻已在上星期五身穿粉紅色馬來服,在下議院提呈2022年財政預算案。
確實,相較以往,本次財案的準備流程稍為開放。8月25日,朝野簽署《轉型與穩定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後,財政部史無前例地在8月31日發佈財案前公告,同時與在野的希望聯盟舉辦了數場工作會議。
當然,這並非個雙方「共同完成」的預算案,充其量只是有個「回應機制」,較為相容的財案流程。其中99%內容,依然由執政集團與官僚體制主導(以下將闡述這種體制慣性為何難以注入新思維、引發改革)。
果不其然,翻開預算案,除了媒體一貫熱衷報導援助金加碼、為冠病撥備資金、振興經濟配套外,並未有讓人耳目一新的政策。首相依斯邁沙比里(Ismail Sabri Yaakob,下圖)說預算案將讓人有「哇」(Wow)的驚喜,看來是開了個不怎麼幽默的玩笑。
 (來源:The Star/BERNAMA)
(來源:The Star/BERNAMA)
歷來最龐大臃腫預算案
沒有了驚喜因素,整體預算案看上去就是史上最龐大臃腫、行政開銷高達2,335億令吉的財案。這不是危言聳聽,明年年中,聯邦政府的債務將突破1兆令吉。另外,馬來西亞99%收入用來支付行政開銷,而新舉的債務,有一半拿來償還舊債。聽起來很可怕吧?是的,我國正處於「挖洞補洞」的窘況。
讓人驚訝的是,這個史上最大的財案,結果竟然沒有解決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合約醫生課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把合約延長兩年。我國公務員一直增加,為何關鍵部門卻沒有固定職位?另外,國盟/國陣政府非常疼惜公務員,主動把累積年假增加至160天、允許80天或50%年假可換取現金,同時讓退休公務員可獲350令吉獎金。但是,財案絲毫未提到如何提升政府效率與減少繁文縟節。除了前線人員,受疫情影響最少的應該是公務員,卻獲得厚待,似乎公僕才是財案的主角而非人民。
是的,以上僅是即席拋出的評論。實際上,我們面對的問題比以上所言更大,影響也更深遠。
拋開種族宗教的叫囂雜音,過去三十年,馬來西亞面對的基本挑戰,是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發展停滯和官僚體制退化。
經濟放緩貧富懸殊日巨
過去三十年,是經濟發展逐漸放緩,但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過程。就算在2016年至2019年,基尼指數依然從0.399上升至0.407。諷刺的是,實施將近五十年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y Policy)精神,專注在分配而非創造財富。然而,就在這個主旋律下,貧富差距竟然持續擴大,甚而使馬來西亞成為亞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真是個黑色幽默。
無論「第十二馬來西亞計劃」(12th Malaysia Plan, 2021-2025)或最新財案,都沒有任何具體措施扭轉這項趨勢,反之可能更加惡化。今天,布城的政治與官僚集團大都系出同一背景,不是寄宿學校就是MRSM(初級科學院校)再保送出國。這些精英的思維高度雷同,生活圈也高度同質化,自認擅長俯瞰政經事務,草民的複雜問題,往往只是呈現在冷氣房大桌上(如今是電腦螢幕前)的一堆資料。
至今,這個集團無意願,也無方法去解決農民、漁民、新村、城市貧困人士的問題。舉個例子,聯合國前專員阿斯頓(Philip Alston,上圖)去年考察後指出我國的貧窮線不切實際,但高級部長阿茲敏阿里(Mohamed Azmin Ali)第一個跳出來否認,就是把貧窮問題掃進地毯裡的思維。
財長提呈財案時只得意洋洋地宣佈提高援助金的數量、上修「援助的基線」,卻沒有上修貧窮線,也沒有遵循聯合國的公認標準,把貧窮線定在個人而非家庭為單位。當局更加沒有取消讓人混淆的「赤貧」(Hardcore Poverty)定義(聯合國並無赤貧定義),足以證明執政精英依然迷失在本身建造的宮殿裡。
 (來源:The Star/BERNAMA)
(來源:The Star/BERNAMA)
體制慣性致令發展停滯
也因此,體制的慣性(Institutional Inertia)導致無論大馬計劃、財案或政策思維,只能夠年復一年延續、強化既有的發展與分配模式。局部修復偶爾發生,卻未根本改變其思維與行進軌跡。因此,當經濟發展弱化至分配出問題時,只能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把問題踢給其他部門導致機構越趨臃腫,或把預算案隱藏在預算外(Off Budget)繼續歌舞昇平。當政府任內沒得再傳球時,就踢給下一代承受。公積金局為退休人士的零丁存款哀嚎時,曾經口出金句「我幫你,你幫我」的前首相納吉還倡議讓國人再提高I-Citra提款,就是經典的例子。當下儘管「我幫你,你幫我」,年邁以後如何體面生活,或下一代負債累累,都容後再說。
同質化與退化的官僚體系,更導致經濟發展的腳步蹣跚。希盟在主張以廢除新經濟政策的精神,提出擬定扶持新興產業的政策,設立更有效率的一站式投資中心來推動再工業化。希盟尤其注重如何在沙巴/砂拉越兩州建設勞動力密集的產業,以擺脫當地對半島的經濟「半殖民狀態」。
另外,在扶貧與護老扶幼方面,希盟也提出解決童婚問題、提供兒童看護津貼,多建社區安老院等主張,頗有亮點。可惜我國社會還是注重身份政治甚於政策辯論,令許多政策無法獲得足夠討論空間,殊為可惜。
抽絲剝繭剖析後,2022年財案缺少的,恰恰也是過去三十年所失去的。諸如此類的財案一再提呈,但世界不會再等待馬來西亞。在首相的「哇」之後,依然是大大的問號。
 李健聰 |
馬來西亞科技與工藝大學交通物流碩士,彭亨州關丹士滿慕區州議員,公正黨總財政,長居關丹。相信基層民主與社區賦權能帶來根本變革,因此積極推動社區營造與民間教育工作,目前推動的計劃包括「士滿慕社區菜園」與「關丹悅讀換書計劃」等。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來源: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