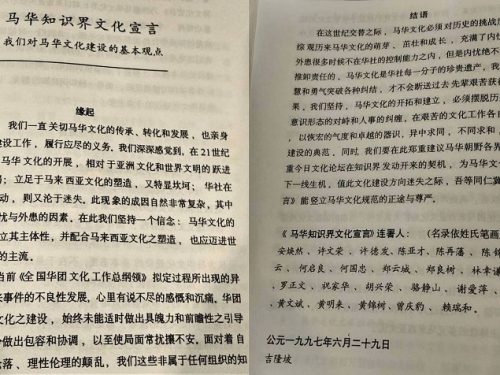(來源:Quartz)
廿一世紀社會不僅應體現族群和文化多樣性,追求人人平等也是普遍認同的理想。當然,面對傳統的權力階層,除了憤怒的潑紅漆和揭發,應該有更多的建設途徑。其中一項可行的方法,就是設法讓體制裡的領導來自更多樣化的背景。管理層若由社會背景高度相似者出任是不健康的,必定會把本身的經驗、價值觀和道德觀視為理所當然。領導層的多樣化,應當成為大多數進步團體的目標,不僅國家、政黨應當如此,民間組織如華團也應有此期許。
【文/吳益婷】
反種族主義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在全球各地點燃對抗的火焰,不僅構成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社會現象,也體現平權概念正在大面積擴張。這個運動令人想起幾年前在西方國家掀起的Me Too 運動,兩者之間的共同點是挑戰了社會上由來已久的權力中心裡多數成員的價值觀。另一個相似點是都跨越國界,延燒至世界各地,獲得來自不同社會的共鳴。
這兩點共同之處的背後,是參與上述社運者的思想覺醒和切身體會,即每個社群或社會中總有一群人掌握比別人更多的權力。他們大多數是國家或政府裡的決策人,影響著國家立法、司法和執法過程中的價值觀。同時也是大型經濟活動的掌控者、社會主流價值觀的捍衛者和受益者。在以白人為主的西方國家,佔據社會權力中心的群體多數是中產階級的白人中年男性。在其他社會,支配社會各種主要體制者,往往也是擁有相似的社會特徵,特別在種族、性別、經濟地位和年齡層,出現高度相似。
本文並非要論證這樣的發展有多不合理,而是想指出所有的社會都有一群同質性相當高的群體支配著各方面的運作,而這樣的結構正受到巨大的挑戰。
 (來源:The Des Moines Register/Andres Kudacki/AP)
(來源:The Des Moines Register/Andres Kudacki/AP)
當然,所有以偏概全的描述都會出現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危險,例如中產階級的白人中年男性肯定也有支持Me Too 和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者。但是無法否定的事實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白人中年男性,遭到性騷擾或性侵和種族歧視的機率遠低於一個年輕女性雇員和黑人,更不用說性騷擾和種族歧視的加害者,很可能是他所認識的朋友、同事、家人和教友等。他們也許會說,自己更容易「理解」性騷擾和種族歧視者的邏輯、掙扎和經驗,甚至同情這些人無法改過自新的「痛苦」。正如性醜聞纏身的知名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對惡名昭彰的哈維溫斯坦(Harvey Wainstein)的「遭遇」是以歎氣的口吻說,「Harvey Wainstein is a sad, sick man。」 在伍迪艾倫的感歎裡,哈維溫斯坦似乎被形容為一個悲哀的病人。如果如此視角頻密地在媒體出現,而且被編輯高調展示,那外界會忽視甚至忘記此人以自身職權長期侵害年輕女性的事實,是一個善於操控她們的慣犯。
過去一年來,馬來西亞的種族關係、歧視議題雖未明顯改善,但處理性騷擾申訴的方式已逐漸轉變。發生在教育界和公民社會的性騷擾事件,都獲得國內各大語言媒體報導,更重要的是,受害者不選擇沉默,各界支援和同情他們的挺身控訴。
回到在十多年前,如果舉報對象是看起來具高尚職業、對社會有功人士,那情況可能是扭曲的。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位曾經性騷擾我朋友的華教人士最近過世後,被歌頌得像英雄一樣光輝。歌頌者卻知曉他的行為,這才令人吃驚。實際上,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後任職媒體時,已耳聞他性騷擾年輕女性的傳聞,許多人卻當成笑話議論。後來我投身教育機構,親自從一些熟悉他的領袖口中聽到這位華教鬥士的行徑。直到網路媒體風行的年代,才有受害者通過部落格公開控訴其舉止。後來,他強抱女記者的新聞上了報章頭條,掀起軒然大波。不過華教領袖們的輿論焦點似乎不是性騷擾,而是傾向於從華教內鬥看待,反而自圓其說成內鬥下的「受害者」。
 (來源:The Star/Art Chen)
(來源:The Star/Art Chen)
為什麼那麼多愛護教育人士可以讓他橫行十多年,直至去世後還推崇備至?原因是他在華教運動中勇於批評政府,畢生立場強硬。由於符合組織掌權者的價值觀,這種「硬漢」姿態的民族鬥士在廿世紀最受推崇。他的行徑,也許在那個世代的同僚眼裡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只是被看成一個悲哀的病人。因此,解決的方法包括協助他求診,提醒年輕人避免接近,但從未採取「損害」其名譽的行動,如報警。
進入廿一世紀,這種推崇民族英雄、掩蓋「英雄」錯誤行為,甚至為其豎碑的做法已受到挑戰。在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裡,那些擁有販賣黑奴記錄的建國民族英雄雕像被潑紅漆、推倒;在Me Too運動裡,一個在娛樂界被視為成就非凡的巨人倒了,為其行徑負上刑責,這些事例都說明傳統價值觀遭到質疑。傳統的英雄人物,很多是來自某個階級、年齡層的父權和種族/民族主義社會。這些英雄事蹟展現在如何征服敵人,讓自身族裔強盛,至於是否蓄奴、蹂躪敵軍妻女則是完全可以忽視的事情。即便有發生,也被視為符合「常理」。那個時代的平權不包括某些種族、性別和階級,後者的遭遇因而被忽略。Black Lives Matter和Me Too運動並未抹殺這些「英雄」在特定領域的貢獻,他們的貢獻早已被記載,也獲得了肯定。這些運動強調的是,受害者的聲音需要被訴說和傾聽,他們的遭遇理應獲得更公平的看待。因此,應該用更進步的價值觀來紀念那些有貢獻人物。
廿一世紀社會不僅應體現族群和文化多樣性,追求人人平等也是普遍認同的理想。當然,面對傳統的權力階層,除了憤怒的潑紅漆和揭發,應該有更多的建設途徑。其中一項可行的方法,就是設法讓體制裡的領導來自更多樣化的背景。管理層若由社會背景(如種族、年齡、性別、階層和教育背景等)高度相似者出任是不健康的,必定會把本身的經驗、價值觀和道德觀視為理所當然。領導層的多樣化,應當成為大多數進步團體的目標,不僅國家、政黨應當如此,民間組織如華團也應有此期許。
 吳益婷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研究領域為砂拉越政治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