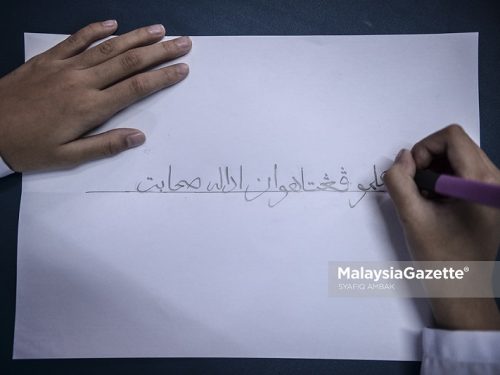(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Felix Wong)
反智未必是盲動或沒有理性思辨的結果,然而人類雖然思考,卻沒有人能擔保其思考的內容與結論。馬新華社本身有尚智傳統,包括推崇讀書人,重視文教,熱衷辦學,深信教育可以促成社經地位的流動。的確,現今父母整體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但學歷卻無法保障他們能用更開明及更開放的態度接納新事物和新觀念。一個人的習慣和觀念沒有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跟進,則產生停滯、落後的效果,使其脫節或作出不合時宜的表現,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所謂「中華膠」的言論、心態和情結,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世代。
【文/潘婉明】
近幾年我開始在臉書上注意到有關「六四紀念活動」的報導及留言,出現否定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過解放軍屠城的觀點。論者全面否認中國政府下令鎮壓學生,還要求他人拿出當年有流血的證據,又一貫指控外國及外媒操弄輿論,捏造學生死亡人數,隱匿解放軍傷亡情況,誇大事態嚴重性,都是包藏窩心的陰謀。
我嘗試梳理及消化這些「嶄新」的觀點,釐清「否決論」的憑藉和脈絡,是如何在堆積如山的證據和罔顧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展開和傳播之際,發現另有「鎮壓(正當)論」異軍突起,早已出現在虛擬世界的平行時空。這派見解延續大中華一統論述,主張武力掃蕩。他們如臨現場,忽而聲稱當年沒有學生遇害,死的都是解放軍,忽而贊同鎮壓有理,屠殺無罪:「沒有六四的鎮壓,就不可能有中國今日的發展和成就」,陷入大國崛起的共榮與想像。
儘管這些論述完全違背我們對六四歷史的認識,它們卻在當今馬新華社自成一方主流。如果說這是中國封鎖新聞三十年有功,則我們可以理解為年輕論者在未有充份資訊下作出的不客觀評論,正如大部分中國人從未見過那張著名的「坦克人」照片。但中年以上的論者究竟為何及如何改變了立場和論述,卻耐人尋味。「中華膠」一詞無疑也是在這種困惑中產生的。
馬新華媒露骨親中
輿情嗜血二元對立
不過,震撼教育有助於增強免疫力,特別是當我們再三面對社交媒體留言之沒有下限時。因此自六月初香港「反送中條例」事態一路發展至今,我們雖對網路輿論嘆為觀止,但也十分熟悉。馬新華文媒體原則上親中,紙媒尤其露骨,網媒則相對兼容,但平面媒體電子化的結果模糊了這個界線,使整體網路讀者乃至於華社的觀點趨同,普遍支持香港特首及政府,維護「一個中國」利益。
 (來源:Imperial Valley Press/Chiang Ying-ying)
(來源:Imperial Valley Press/Chiang Ying-ying)
馬新華人對中港台政治進程和動態有異於其他地區的熱忱,唯論述僵固,難以撼動。舉例而言,馬新讀者對台灣政黨政治及選舉消息異常關心,不吝批評,但觀點乏善可陳,即無條件支持國民黨,堅決反對台獨,對一切分裂中國的言論義憤填膺。此番對香港連日「反送中」抗爭的發展,馬新言論除了一貫的輕蔑和憤慨,還多了惡毒與涼薄。
綜觀網路言論,馬新華人廣泛支持林鄭、認同港共政府、力挺前線警察、譴責學生暴力。因此留言輕則以不屑、戲謔的語言嘲諷「反送中」人士,或以污言穢語辱罵學生為「廢青」、「垃圾」,皆為外國勢力所利用;重則鼓吹武力,支持警察鎮壓,樂見解放軍接管,無視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輕賤他人性命。
馬新輿情嗜血暴戾,卻也以「暴力」做文章。他們咬死學生擲磚頭、持鐵枝,對警棍、催淚彈、胡椒噴霧以及執法過當視而不見。不少人提醒馬來西亞華社,BERSIH那些年我們不也吃警棍、避催淚彈、躲胡椒噴霧和化學水車,理應基於共同的投身革命經驗和情感,對香港抗爭者產生更多同理心。但論者以為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我們具有和平、反貪、推翻暴政的正當性;而他們襲警、衝撞立法會、破壞公物、受外國勢力干預、阻礙香港發展、反中、港獨。
雖然網路評論不能反映全部意見,而當今又是網民及網軍崛起的時代,虛擬世界既無國界,也無真實面目,使我們很難斷定留言者的真實身份。不過,當社會出現大量同性質言論,也值得我們正視和探究。不少評論人和學者也注意到輿論分裂成兩派,彼此以「中華膠」和「慕洋犬」相稱相罵,二元化對方的立場,一般的分析歸因於華人在國內處境的投射以及根深柢固的大中華情結使然。
網路展示獵殺姿態
虛擬世界惡毒涼薄
正當「中華膠」和「慕洋犬」為香港前途爭得面紅耳赤欲罷不能停之際,另一起意見嚴重分歧的國內罵戰悄然登場。一名女性華裔初中學生因辱罵男性馬來教師為「阿瓜」而遭後者鞭打,學生母親到校投訴繼而報警,但由於家長態度囂張,事後又將為女兒討公道的影片上載到社交媒體,結果反而引起全國性的撻伐。輿論一面倒支持老師,任何指出不當體罰及教師情緒管理問題的言論,也一概被簡化及扭曲為認同虎媽、嬌縱孩子。
「阿瓜事件」來勢洶洶,數日間出現不成正比的訊息留言量,鬧騰一時,卻又迅速以師生、親師握手言和落幕,平息得不留痕跡,足可見這是社會普遍關心、廣泛面對並且長期膠著的課題。的確,事件最大的爭議在體罰,而體罰是我們成長的年代始終掙不脫的正當暴力,包括家庭的,和校園的。
 (來源:Berita Harian)
(來源:Berita Harian)
體罰如同反撲的獸,體罰世代熬成家長以後非但沒有從暴力枷鎖中解放出來,反而更加認同藤條的功能和效力。當我們不齒張狂的潑婦罵街,當我們被沒有家教的孩子激怒,我們就群情激憤,祭出藤條,而未察覺鑲嵌其中的權力關係與道德審查。成年男性教師和十三歲女學生分別在各自的教/學位置上,而這個身份本身就是權力關係,加上性別和身體的差異,以及社會對「非典型女孩」的厭惡和作用,這些本應該是我們獵殺這個少女之前必須考慮到的。
然而我們沒有。我們摒棄了愛的教育,否決愛及教化的可能性。相反的,我們等著看她敗壞腐爛下去,我們尤其想看看她媽媽怎麼出洋相。我們也站在「友族」的立場來理解男教師所面對的文化處境與宗教壓力,體諒和包容他的情緒出口,以支持體罰作為對他的聲援,用這樣的偽正義和溫情來抵銷我們對女孩的殘忍、毒舌與拋棄。
無論是遠在他方的國際局勢,或近在咫尺的切身日常,網路所展示的惡毒的話語、涼薄的人心和獵殺的姿態,都已經不是虛擬世界或鍵盤英雄之類分析框架足以充份說明的了。網路留言改變了人們發言和對話的形態,使用者不再受身份、時間、對象和距離的限制,隨時參與,隨便進出,自由闡發個人意見,從而晉身「網路公民」。
不過「網路公民」的言論並沒有超出反動修辭的架構。根據社會學者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 1915-2012)的理論,人類文明不乏反對進步思想的歷史,但保守主義擅於利用不同的語言策略來包裝及為其反動辯護。反動的修辭有三種公式,首先是適得其反的「悖謬論」,例如:「我認同民主政治,但你看看台灣就是太過民主才會這麼亂!」然後是徒勞無功的「無效論」,例如:「我贊成民主政治,但只有民主無助於經濟成長,不先解決民生問題,社會再民主也沒有用!」最後是顧此失彼的「危害論」,例如:「我支持民主政治,但他們三天兩頭示威遊行,已經危害到社會穩定和公眾安全了!」
反動修辭包裝保守
反智放任誤會偏見
赫緒曼認為,保守主義者因為羞於啟齒而不敢公然反對進步主張,唯有提出反動的修辭來偽裝自己。但這個在前網路時代提出的分析框架顯然已經跟不上科技形態和人心變化的步伐了。當今網民已進化到沒有甚麼是不敢啟齒的,他們大剌剌地主張鎮壓,罔顧人命代價,三十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三十年後香港街頭上的「廢青」都死不足惜!
體罰的爭議亦然。輿論廣泛支持體罰,教師和家長達成共識,形成難以撼動的共犯結構,反使愛的教育寡不敵眾,淪為邊緣。根據網路判讀,絕大多數留言公開支持家庭及校園行使暴力,儘管也有拐彎抹角的反動修辭,但更多的是大方承認,而其中不無理性思考和實證傳承。也就是說,家長和教師傾巢而出,而他們的論點是以實踐為基礎的,非但可以突破反動修辭所得出的「無效論」,更可以坐實相反方的「危害論」:愛的教育只是溺愛教育,愛他適足以害他。
 (來源:星島日報)
(來源:星島日報)
因此反動辭修已不足以分析上面各種論述和立場,但反智力量或許可以幫得上忙。弔詭的是,馬新華社本身有尚智傳統,包括推崇讀書人,重視文教,熱衷辦學,深信教育可以促成社經地位的流動。的確,現今父母整體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但學歷卻無法保障他們能用更開明及更開放的態度接納新事物和新觀念。
歷史學者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在其《美國的反智傳統》一書中指出,反智傳統的形成出於公眾對現況認識不足,對智識感到畏懼或不信任,而沒有足夠寬闊的視野作出客觀的判斷,又放任自己的偏見和誤會,在錯誤的基礎上擴大誤解。
我認為這個分析框架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網路言論的現象。反智未必是盲動或沒有理性思辨的結果,然而人類雖然思考,卻沒有人能擔保其思考的內容與結論。如果再加上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提出的「滯後作用」,即一個人的習慣和觀念沒有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跟進,則產生停滯、落後的效果,使其脫節或作出不合時宜的表現,可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所謂「中華膠」的言論、心態和情結,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世代。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