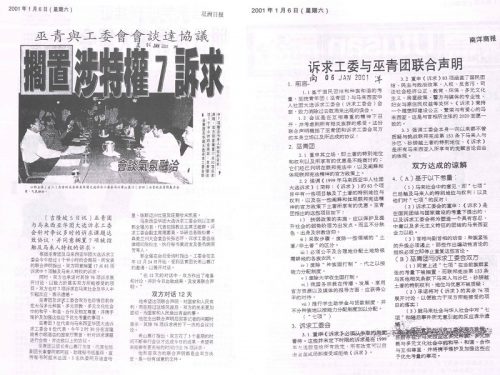(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EPA)
馬來西亞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並未因國家領導的更換而消除或减弱。政權更迭與制度或結構改革同等重要,兩者互相形塑,久而久之便形成文化。公民組織比選前更忙碌,一方面爭取向新政府陳述政策意見,也促成跨族群與文化交匯,產生新共識和文化。選後的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惟公民組織發現形塑社會共識的可能性增加了。在當前政治氛圍下,馬來社會的多元性比之前更從容開展,勢必重塑未來社會的主流觀念、共識。
【文/吳益婷】
第十四屆全國大選後,我出席了幾個評論選舉結果的講座,其中一場的講者不約而同表示,目前還在變天後的蜜月期,感覺暫時可以休息一下,暫時想信任新政府。一晃八個月過去了,此時此刻,對許多公民組織而言,變天的蜜月期已經結束,目前需把精力集中在過去被「改朝換代」目標所擱置的社會與利益矛盾問題。
選舉成績和不同政黨的席次分佈,讓社會分歧具體化。絕大多數希盟支持者是馬來半島西海岸選民,這區塊是國內商業活動最蓬勃、城市化最高的地方。西海岸選民對國家的期望、如何實現國家願景,與西馬東海岸和東馬沙砂兩州似乎有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指標是選擇的政黨:西海岸選民投希盟政黨,東海岸投伊斯蘭黨和巫統,東馬兩州比較偏向本土政黨。這樣分法雖然十分粗糙,但確實浮現這個趨勢。
本文不談宏觀的社會矛盾,而是微觀的,我接觸到的社會分歧,主要以語言、文化和生活環境的差異爲分歧點。我認爲這些分歧也影響他們的政黨或政治選擇。
過去半年來全國關注政府對承認獨中統考文憑的態度。非馬來人的公民組織幾乎一面倒支持承認統考,但是馬來人組織,包括多數自由派馬來知識份子(如伊斯蘭復興組織領袖)則大多數反對或有條件支持。針對統考議題,幾個重量級華人文教組織曾與伊斯蘭友好協會(IKRAM)對話,我有幸參與,過程十分融洽,但仍無法說服對方承認統考。跟伊斯蘭友好協會立場最接近的是伊斯蘭青年運動(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ABIM),也堅持要考獲大馬教育文憑(SPM)歷史科和馬來文優等條件。在馬來亞大學廣場,也有青年學子公開對話,解釋支持和反對的立場,過程友好和平。對此議題,我看到社會普遍認可獨中統考的學術水平,問題的關鍵是語言和文化差異。新政府至今仍在拖延,尚未落實這項競選承諾。
另一矛盾是由巫統和伊斯蘭黨推動的反「反歧視公約」(ICERD,《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大集會,成功動員數萬人聚集吉隆坡市中心。在這議題上,伊斯蘭友好協會表示沒有簽署必要, 伊斯蘭青年運動卻認同需消除歧視,至於非馬來穆斯林幾乎一致支持政府簽署公約。不同立場公民組織對此多番對話,也各自發表聲明,但後來感受到馬來群衆的强烈情緒,便决定暫緩對政府施壓,政府最後也決定擱置簽署ICERD。
媒體高調報導上述兩個議題,我們不難看到不同族群因語言、文化態度産生的分歧。實際上,另一分歧是族群內部的文化或價值觀之爭。在我的任職機構——馬來亞大學時常出現文化角力。 過去十多年來,馬大掌校者都是理工出身的學者專家都樂於面向國際社會。他們的策略都是要加强英文,認爲英語是國際化、掌握專業知識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們掌校以來,大學各種學術評鑑和考核制度都尾隨西方學界,如博士論文審核,須有資歷相當的外國學者參與;鼓勵各系招收國際學生和聘請外國人爲訪問學者;學術升等取決於在國際期刊(以英文期刊爲主)的論文發表篇數。這個階層多數曾受惠於政府獎學金,早年留學西方,一直與西方學界關係密切,矢志把馬來亞大學擠入世界頂尖大學排名。
上述規定嚴重打擊以非英文發表學術報告的學者,以文學院和馬來研究院最受影響。校方以理工科標準評鑑,使得文學院不論在學術成果和申請研究經費上,時常落在其他學院之後。在文學院已有幾個科系準備增加英語教學吸引國際學生。當院會議作出宣布時,雖偶有異議,多數人仍保持沉默。
擁抱實用科技的科研人員與族群個性濃厚的文化群體,存在著一定的張力和資源競爭。前者由工業和商業化較濃的中産社會文化培育,後者則受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和西方學理滋養,在馬來亞大學,前者顯然佔支配地位。在論述上,那些扎根「族群語文」土壤的研究者,被視爲徒具「甘榜英雄」(jaguh kampung)視野,不符合馬大與世界接軌的願景。這類情况也出現在我之前就讀的檳城理科大學。這是隱藏在政府體制內的文化之爭,如此角力在馬來族群內持續發酵。
另外,在某些看似與語言、族群和宗教無關的議題如地方政府選舉,其支持者也集中在吉隆坡、檳城、新山等大都市,在鄉鎮卻熱不起來。鄉鎮選民雖踴躍投票選聯邦和州政府,對地方政府選舉並不熱衷。雖然伊斯蘭黨把議題族群化,宣稱地方選舉會讓華裔掌控城市,不過鄉鎮的非馬來人似乎也不特別關注地方政府選舉。
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並未因國家領導的更換而消除或减弱,那509改變了什麽呢?變天換了中央領導層,體制上不再一黨獨大,而是背景更多元的領導班子。根據最新民調,逾半馬來人視希盟馬來領袖爲「自由派」精英,對領導層裡爲數不少的「行動黨」人感到不安,因爲他們不認同馬來主權。
政權更迭與制度或結構改革同等重要,兩者互相形塑,久而久之便形成文化。過去幾個月來,我接觸到的公民組織比選前更忙碌,一方面爭取向新政府陳述政策意見,也促成跨族群與文化交匯,產生新共識和文化。選後的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惟公民組織發現形塑社會共識的可能性增加了。在當前政治氛圍下,馬來社會的多元性比之前更從容開展,勢必重塑未來社會的主流觀念、共識。
 吳益婷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研究領域為砂拉越政治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來源:
(來源: (來源: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