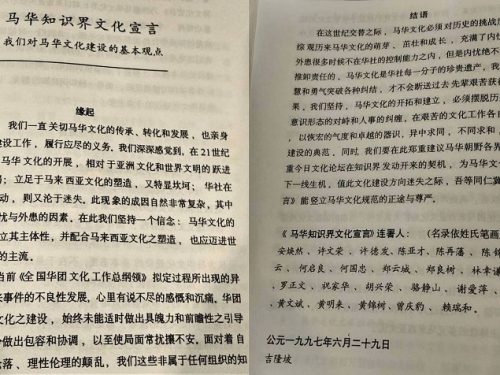(來源:The World Sikh News)
對死刑的討論,必須擴大到關心整個司法、刑罰制度、監獄管理、囚犯心理、犯罪成因、受害者保護、加害者家屬、獄卒福利等方面。監獄不僅僅是體現懲罰或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已,還有很重要的教化和改造功能,體現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如果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知識與教化而改變,相信生命可以影響生命,就必須更深入全面地探討監獄的教化功能。人們對邪惡的怨恨、不安、恐懼,以及各種無處安放的情緒,在廢死爭議中不可迴避。但暫且跳脫受害者的立場,嘗試聆聽和理解各方觀點,是所有公共討論的必要前提。
【文/鄧婉晴】
死刑存廢自今年10月忽然成為全國話題,許多討論儼然從挺廢死和反廢死的角度出發。本文不想直接跳入死刑是與非的爭辯,只提出就此議論的觀察發現。
倘若長期關心本國廢死議題,或翻看媒體過往的死刑議題的報導,即可發現馬來西亞打從2011年開始,就不時提出要往廢除死刑的方向邁進。箇中進程,許多論者已撰文指出,在此不贅述。
廢除死刑是少數在前朝和當今政府都嘗試推動的議題,也是許多倡議組織和遊說團體多年來努力的結果。儘管有陰謀論者認為希盟政府倉促修法廢死,是為了引渡被關在澳洲的蒙古女郎案關鍵人物西魯(Sirul Azhar Umar),但政府在廢死路上也著實非一蹴而幾。問題是,為何政府此前決策動向,並未引發社會關注?政府和倡議組織在決策階層中遊說之餘,推動民間對死刑議題認知的努力是否充足?
 (來源:Flickr)
(來源:Flickr)
民間教育不足 培力管道闕如
馬來西亞主要倡議廢死的組織,包括反死刑與酷刑組織(MADPET)、國際特赦組織馬來西亞分會(AI Malaysia)、人權委員會(SUHAKAM)、人民之聲(SUARAM)、律師公會、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除了MADPET以廢死為唯一訴求外,其他組織只將廢死視為其中一個要爭取的人權議題。其中又以隆雪華堂民權委員會為唯一一個以中文為主要媒介語,且多次舉辦活動傳達廢死訊息的民間團體。但與此同時,前者也關心原住民與水壩、拘留期間致死、母語教育議題等,廢刑只是其中一項關注的人權議題。
2015年和2017年,亞洲反死刑網絡(Anti-Death Penalty Asian Network,ADPAN)和法國共同反死刑協會(Ensemble Contre la Peine de Mort,ECPM)分別在吉隆坡召開區域大會,世界反死刑聯盟(World Coalition Against Death Penalty,WCADP)的各國組織代表無不參與討論。我有幸出席兩次會議,見識到廢死議題涉及範圍之廣泛,從中獲益良多。
可惜這些長期經營的網絡和區域討論,往往局限在特定組織網絡、以英語為主要媒介語的圈子,許多豐富的討論內容也鮮有事後整理或通過網路分享。這固然與人力不足直接相關,許多倡議或參與者本身也有正職,活動結束後就返回各自崗位繼續努力。但這也明顯暴露出倡議組織從區域會議所獲的資訊和培力,並未充分擴及民間,或向普羅大眾進行類似培力(empowerment)活動。
馬來西亞的倡議組織長期傾向直面遊說政府和決策階層,期望能通過修法,由上而下、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以至疏於經營、深耕草根,讓一般民眾對特定議題的認識,經常與政府或民間團體的認知出現落差或斷層。
長期關注議題者固然可輕易認為,那是因為大眾毫不關心,無論如何推進也於事無補。社會一向缺乏公民教育與思辯風氣,過度信任代議士會把問題處理好,也是議題無法在民間發酵的原因之一。然而,倡議組織要對特定議題的遊說,恐怕也需在策略上調整,才能讓長期經營的課題容易進入大眾視野。舉例來說,如果MADPET是國內以推動廢死為唯一訴求的團體,關心議題的人若要尋找更多與本國廢死的相關資訊,在網上只發現它以部落格形式張貼聲明,試問如此傳播、經營方式是否真的有效?
要讓議題深入民心,我們需要更多的語言、更多的故事、更多的視角來談論。但是這一切都需要熟悉此議題的人領頭先行,讓資訊更廣泛地在民間流通穿行。
 (來源:Front Desk)
(來源:Front Desk)
要全民討論須先公開資訊
對目前的討論的另一層觀察是,在地的死刑數據和資訊不完整,甚至闕如。
許多人質問,廢除死刑若以監禁三十年取代,納稅人不就要養他們三十年?事實上,根據知情者在廢死研討會的報告,死刑犯在被裁決之前需經過的審訊可長達十年,如此冗長期間,只能單獨監禁,即使被判刑後,也有者繼續監禁二十、三十年還未被處死。因此納稅人一直都在「養」死囚,而且養死囚比一般囚犯的花費更大,目前國內監獄已過度擁擠,一間原本只能住下十五人的大牢房經常擠入三十人,飲食、衛生、醫療福利等都極不理想。
要真正了解有多少稅金被分配到監獄,就必須擁有真實數據才能展開辯論,否則一切討論難免有一定的主觀推測。為什麼之前沒有人不滿本身所納的稅,會被用來照顧囚犯?因為我們對此事一無所知。
許多國家的監政制度規定囚犯必須勞動生產,自己賺取生活費,甚至償還受害者的訴訟費。為何馬來西亞監獄沒有讓囚犯自給自足的系統,即使在獄中也有生產力貢獻經濟?如果死刑有可能誤判,多年來究竟有多少案例?
印度新德里法律大學在2016年公佈一份《死刑報告書》,在2013至2015年間在該國各地對373名死囚問卷調查與一對一訪談。調查結果顯示,高達74.1%死囚來自貧窮家庭,是經濟弱勢;63.2%死囚是家裡唯一經濟支柱;61.6%死囚未完成中學教育;76%死囚屬於低階層及宗教弱勢;80%囚犯曾在監禁期間受到暴力;71.4%死囚在最高法院審訊時沒有個人代表律師。諸多國外研究都顯示,死囚會犯罪與其成長背景和社會階層密切相關。馬來西亞至今有無相關研究可供參考?
馬來西亞實行秘密執刑(secret execution)制度,一般在星期五早上問吊。死囚家屬通常在問吊前兩天,才接獲政治局通知,必須盡一切可能趕去見最後一面。就連倡議廢死長達四十年的國際特赦組織也沒無法取得死刑相關數據,只能從媒體報導統計每年最低處決人數。他們每每在家屬投報求助時,才知道誰會被處決,才能行動向元首請求赦免。秘密問吊不僅讓死囚家屬長期擔心受怕,也讓倡議組織無法更有效地進行聲援。如果死刑是罪有應得,為何政府不能直接提早公開或安排受刑犯的問吊日期?如果死刑是用稅金執行「正義」和懲罰,那就關乎公眾利益與安全,有必要公開更多資訊。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外界只能根據自己對刑法的既定印象和模糊觀感來判斷。這樣的討論無法看清每個個案的脈絡和處境。
廢死組織經常引用馬來西亞在2013年針對強制死刑的一項調查《死刑報告書》來印證,當人們對真實的案情知道更多細節,他們對死刑判決的疑慮會更小心,直接支持強制死刑的人也大幅減少。可見資訊公開對公眾思辯有著直接的關係。
 (來源:AP News/Sadiq Asyraf)
(來源:AP News/Sadiq Asyraf)
不應只體現懲罰或應報正義
監獄裡究竟有誰?我們為何需要關心?許多人一想到殺人者無需賠命,就深感忿忿不平,認為對受害者家屬不公平。受害者無辜被殺害,殺人者沒有權利要人權。歸根究底,我們都希望社會能彰顯公義,做壞事就要受到成正比的懲罰。我們更希望如果有一天自己或身邊親愛的人不幸受害,會有人來為我們主持公道。
我們習以為常地將監獄視為懲治犯罪者的垃圾場。只要做錯事的人被判刑,關進監獄,被排除在外,社會上就少了一個「人渣」,不論販毒者、持槍者、還是殺人者,我們都能遠離他們一點,這個社會大概就會安全一點。只是死刑議題遠遠大於懲罰與報復,那攸關一個人的性命被國家不可逆轉地永遠奪取。我們如何看待國家奪取個人性命,關乎我們如何思考「正義」,如何看待「生命」,如何想像「監獄」,以及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
受害者家屬憤恨難當,死刑能洩恨,無論死刑犯最終受刑與否,家屬依然背負深沉巨大的失落與悲痛。多年來社會有沒有支援系統給予保護、陪伴和足夠的照護,讓他們不那麼孤獨地啃食悲痛?社會習慣在事件發生時熱烈地報導,但回歸平靜後,家屬的日子如何過,卻不是我們能夠想像的。這個照護系統,不是讓加害者受死就完結,而是需要年復一年的輔導與陪伴,但這部份卻是目前的討論鮮少觸及的重要面向。
如果受害者家屬能有足夠友善的支援系統來處理內心傷痛,他們對世間的恨會不會減少一點?除了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其實也一樣需要關注。加害者如果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執刑後家屬一樣失去依靠,更糟的是,因為加害者「該死」,家屬的傷痛更難以言說。曾經在研討會中聽到一位加害者家屬現身說法,提到殺害憂鬱症妻子的哥哥自小家貧,沒受幾年教育,也和家人關係疏離。哥哥出事後的每一次審訊,他都請假和律師一起出席。他不知道可以做什麼,也不知道可以到哪里尋求支援。每一出門,左鄰右舍都在竊竊私語,案發時在家裡目睹經過的兩個女兒,一個七歲,一個三歲。大女兒只要聽到舅舅提起此案,就會沉默哭泣。
死囚的子女背負的社會標籤,會直接影響下一代的行為和思想。我們的監獄制度和法律制度,可以如何盡最大能力保障家屬,減少罪犯在同一個家庭輪迴?
關於死刑的討論,必須擴大到關心整個司法、刑罰制度、監獄管理、囚犯心理、犯罪成因、受害者保護、加害者家屬、獄卒福利等方面。監獄不僅僅是體現懲罰或應報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而已,還有很重要的教化和改造功能,體現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如果我們相信人可以通過知識與教化而改變,相信生命可以影響生命,就必須更深入全面地探討監獄的教化功能。目前國內監獄制度是否具備讓囚犯更生的措施和思維?
 (來源:Malaysia Gazette/Affan Fauzi)
(來源:Malaysia Gazette/Affan Fauzi)
建立認知 展開對話之必要
今年10月初的「人權電影節」(Freedom Film Festival),主辦單位在閉幕當天播放一部仍在拍攝的紀錄片《Menunggu Masa》。本片由兩位律師掌鏡,故事主角Mainthan a/l Arumugam因謀殺罪被判死刑,但他堅持自己沒有犯罪。他在獄中已經十四年,審訊十九次,即使律師找到新的證據證明他的無辜,他依然未知生命的最後一刻何時會到來。放映當天,家屬到場,孩子都已經長大。【延伸閱讀:The Star】
民間需要更多由下而上的努力與跨界,在支持和反對聲浪中,撐開討論生命的空間。媒體應更積極地觸碰以上論及的其他面向,而非圍繞在民眾是否支持死刑上做文章,加深正反雙方的對立。臺灣雖然至今仍保留死刑,但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簡稱廢死聯盟)長期耕耘死刑議題的努力值得參考。只要進入網站,映入眼簾的便是大眾經常辯論不休的質問,以及組織聚焦施力的工作。倡議組織有意識地經營網絡,建立平臺與「據點」提供完整、清晰、有理據的論述,在人手一機的網路時代特別重要。將重要的記錄保留與公開,讓有興趣者隨時可跟進討論,媒體也能得到專業參考,不至於在相同問題上打轉。
固有的論調顯然已經無法滿足大眾的質詢。要全民辯論,政府必須著手公開相關數據,鼓勵問責;倡議組織則應將自身在運動中累積的知識和經驗,釋放到民間。如果能善用新媒體和科技賦予的自由、開放和共享特性,政府和倡議組織本身就可以創造「運動媒體」,用本身的頻道和管道直接面對大眾,減少媒體的中介,讓社群更貼近組織本身傳達的訊息,不用一直援引國外案例。
此次的廢死爭議引發諸多討論,也許是政府始料未及的。這一次,許多網民開始發現,票投希盟並不保證政府往後每一項決策都是你認同的。隨著國人積極關注公共議題,政府和相應組織需讓更多資訊與知識流通,才能在時機來臨時,有足夠資源深化討論,推動社會進步。人們對邪惡的怨恨、不安、恐懼,以及各種無處安放的情緒,在廢死爭議中不可迴避。但暫且跳脫受害者的立場,嘗試聆聽和理解各方觀點,是所有公共討論的必要前提。
 鄧婉晴 |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畢業。之間文化實驗室、84號亞答屋圖書館成員。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